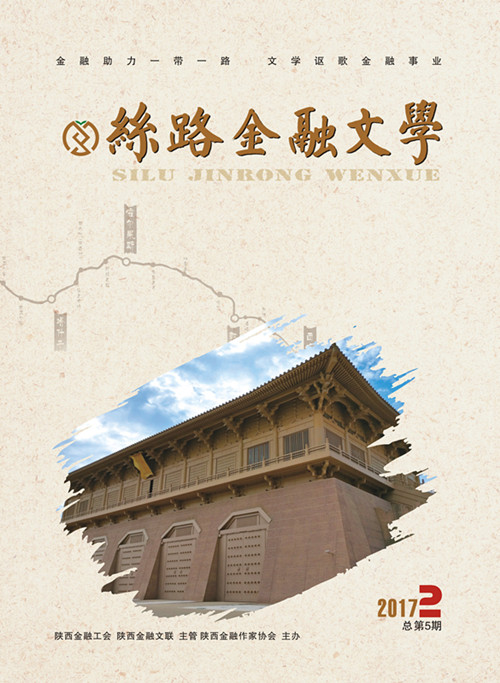适逢益鹏兄的评论文集准备结集出版,要求我对他所写的东西说上几句话,对于这样的事情作为金融协会的同仁当然愿意鼎力相助,于是就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把他的文章前前后后看了个遍,有的地方还反复看了几次,才觉得有说一些什么的底气。但一旦开始落笔,又不免产生许多的犹疑,看完他所写这些东西之后实际上产生了更大的犹疑。益鹏在他的书中为这么多陕西文学界的大咖写了评论,他实际上尽可以请这些大咖中的一个来还他个人情,让我这样一个才学有限的无名之辈来对其文字鼓噪一番,多少有些勉为其难。有了这样的疑虑之后心理不免有些惴惴,于是颇悔当时不知深浅地就应承了这件事情,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希望自己能勉力弄出一篇还算像样的东西,来报答益鹏的知遇之意。而世间的事情似乎都是这样,态度一旦端正起来,倒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对于这段时间的心境,可以化用益鹏在《扶贫,一个庄严的命题》中的文意来进行表达:这段时间真是庆幸自己接了这份苦差事,感觉没有虚度这一段的时间和光阴。也因此,我在这里用了杜甫《蜀相》中的两句来作为文章的标题,因为我下面所发的感叹,言此似乎也不在此,既谈我因为益鹏的文学热情所生发的一些感想,也想透过益鹏的文字远眺世人那忽远忽近的文学之梦。
本来文人的模样
仔细读罢益鹏的这些文字,对他所写的东西大致有了一些掌握。在文中,益鹏将这些东西做了大致的归类,分为了“文人相亲”、“文坛杂议”、“文章小评”这样三个部分,但总体上来讲文章所涉内容还比较杂,看的时候颇有些眼花缭乱之感,这也使我对如何来把握这本书的主线颇费了一些思量。从所写内容来把握吧?所涉及人物,上至贾平凹,下到他一路走来的文学同道乃至他上一辈的张永华老先生,人物跨度如此之大,还无法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来评述。那么从所写的形式来进行把握?整本书中,益鹏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陕西散文协会中的种种见闻,谈了他在散文上的抱负,此书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是他从事散文写作的一种实践。但是从文体把握的熟练程度上来讲,虽然益鹏不时会自得地提起他先前创作的《恍然如梦》这部长篇小说,但益鹏的文学基石还是应该落脚在诗歌方面,可以看出他曾经在诗歌上下了不少的功夫并且对此颇有一些心得。
既然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无法对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一番梳理,那么我们还是回到益鹏这个人身上,知人论世,庶几还能从其文章中找到一些更为深入的东西。对于益鹏这个人,其实我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进行形容,就像福楼拜要求莫泊桑的那样,找到一个最准确的词来对应这个人。但可能是我的功力不够,也可能是益鹏还不够典型,搜肠刮肚一番之后,最终只是借助于“文人”这个稍显空泛的词。因为在我看来,即使益鹏一辈子从事的是银行的工作,但他给我的印象本就是一个“文人”,甚至还偏于旧时文人的模样。在文学的世界里能够做到自得其乐。像是他在《借贾老师的“静虚村”一用》说的:“这只是一个人的村庄,如同刘亮程的散文之于西北大野。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守住一方清静,摈弃私心杂念,在心灵的土壤任意栽种,或谷、或稻、或花、或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如此这般,岂不也是老庄之求,人生至境么?”
能够在一个普遍粗鄙的时代被称之为一个文人,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因为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是一个文人,其实还不是在单指他具有多高的文学才华,虽然文学才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像是益鹏在书中提到的贾平凹、肖云儒、方英文、陈长吟这些人。这些人之所以被人称之为文人,大抵是因为从一个专业的分工的角度上其文学才华被世人所认可。而至于益鹏,他一个原本的金融界人士,整天忙于替人“数钱”,但却比很多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本来文人的模样,这就不光是因为他人长的白白净净,一直戴着一个账房先生式的眼镜,更多地缘故应该归于他对于文学的一片痴心。益鹏在书中讲到,上世纪90年代,当从报刊上得知“陕军东征”的消息,就坐车70多公里,从岚皋赶到安康新华书店,一次购齐了“东征”的五本书,之后便时常摩挲,内心与有荣焉。在《拜谒柳青,遇见四杰》中他还写到:“如今,签名似乎已不被人看重,但在我眼里,让自己崇拜的作家亲书大名于扉页,一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爱屋及乌之情真可说是溢于言表。
在日常的接触中,益鹏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老好人、实干的人,别人不做的事情他来做,别人不干的事情他来干,是一个谦逊低调,甘于吃亏的人。读罢这些文字,我才突然发现益鹏身上还有不太为人所知的倔强一面,这应该也是文人的一种标配,让人很容易想起鲁迅笔下的柔石。他在《拜谒柳青,遇见四杰》似在与人争辩地申明:“作贾老师的“男粉”咋啦?向陕西泰斗级的大作家弯腰,我心甘情愿,深感自豪,不觉得丢人。”想着他瞪着眼睛,有些口吃的论辩模样,使人不禁莞尔。这样的倔强在文中也时不时地出现,像在《今天,我被红孩的散文灌醉了》中他又言道:“身为中国散文学会的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的红孩,可以说是阅人阅文无数,我自己有几斤几两是用不着别人提醒的。” 想来益鹏在文学上与人争辩已成为了一种习惯。
这种因为文学而与人争辩的习惯,也说明益鹏作为一个文学圈外的人物,对于文学,根本就不把自己当外人,把文学圈当作自己一亩三分地,对其中的代表人物更是表现的心悦诚服。在《送别红柯》中他这样表露自己的心迹:“过去,我是排斥与名人合影的,原因如女儿所说:不想蹭名人的热度,沾名人的光辉,有本事,自己去闯出一片天下。但我明白,这只是一句‘年轻气盛’的话,该服输就得服输,喜马拉雅山也并不是人人都能翻越的。崇敬一个人,不会让你变得更矮小。”对于益鹏来讲,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更不是一种自我标榜。如果说有什么私心,那么他真心地把陕西文学所取得的成就视为自己的荣耀。这样的情感应该就是康德所说的比较稀少的“纯粹”吧。这种纯粹除了跟个人的性格相关之外,更多应该是来自于发自内心对一个东西的热爱。
文似波涛情似海
既然讲到了纯粹,那么在看益鹏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仔细分辨他在文学上的付出、收益以及还未完成的雄心壮志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应该把文学作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命中本质的东西。正像他在《文学的别名叫青春》中所言道的:“此后,我从镇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省,无论工作地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无论家庭曾经历了怎样的贫穷与困顿,对工作的踏实认真态度始终没变,对文学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始终不移。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言:这些年来,无论动笔也罢,搁笔也罢,心中总是不灭那盏希望的灯,总是默默地告诫自己:那是你作人的骨头,不要轻言放弃。要相信自己。也许,你这一生都将难以走通那条路,梦想永远只是梦想,但你得以自慰的是,你为之奋斗过,被她鼓舞过,荣耀过。在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程中,她充实了你日渐枯瘦的内心,迫你逼视人类,升华灵魂,明白许多立身处世的道理。至此,只要心头依然光明,多些曲折又何足道哉!”益鹏之于文学,真可以说是不争而争了,已经化成他骨血的一部分。
通观益鹏这本集子,大致类似于散文集或者杂文集一类的东西,体现出这些年他学习散文的成果。而从散文本身来看,散文写作说容易也容易,不外乎兴之所至,“我手写我口”,以情绪为主线,以文抒情,为文生情,连缀成篇。但散文写作同时又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其中又蕴含着无穷的变化,一追求穷形尽象,再追求删繁就简、大道至简。对于益鹏这样一个内在真诚直率充满热情的人来讲,掌握情感的直率表达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要真正驾驭文字的无我之境含而不露,似乎还与他的性格特质表述方式还存在一些冲突。当然,散文的生命力就在于无所谓什么金科玉律,只要气韵生成,保持首尾贯穿,就可成就一篇天机弥漫的生动华章。
应该说从学习的角度来讲,益鹏体现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他在不断地揣摩临习过程中,笔锋越发呈现出洗练老辣的特点。比如他在写陈长吟时,不知道是不是为陈先生的文字或者为人所感染,文笔一下变得灵动了许多,“我平时不怎么喝茶,但陈老师泡的茶,我一定得喝,一则盛情难却,二则陈老师的茶,如同他的散文,品质都不低,尝一尝,绝对没有坏处。他尽了心,我随了意,两相得宜。”他在《风雅云儒》的文末,突然冒出这样一句,“祝愿和祝福的话语亦无需多说,有秦岭在侧,铭记在心。”这样的句子,足可被称之为天外飞仙。他在写红孩的时候这样说:“今天的聚会虽在酒店,却并没有沾酒。虽未沾酒,但却被红孩老师的散文灌得酩酊大醉。” 这样的修辞生动而不生硬。在《主席与我抢着买单》中,他说:“走出大门,抬头看天,头顶,一轮月儿又圆又亮。时值深冬,身上虽有些寒冷,但心里却很温暖。” 读来令人感觉温馨。在《广虎寄我两本书》中,他这样写:“感谢广虎赠我美酒两坛,容我日后慢慢品味。闲言碎语,聊作开封辞。” 文字干脆利落,收束的非常巧妙。
应该说以上这些文字都达到了较高的修辞水平。从这样的角度上来讲,益鹏于散文一隅应该算得上登堂入室了,这可以看出益鹏在写作方面的具有极强的领悟能力。另外,看益鹏的文字,总是会发觉其中涌动着的一种强烈的激情,这实际上是他文章的主要特色。不管在你看来这种强烈的情感与益鹏铺张扬厉的文风相辅相成也好,还是与散文所追求的含蓄蕴藉相冲突也好。总而言之,益鹏的文字当得起文似波涛情似海的评价。他在文学的世界里寻寻觅觅,虽不至于冷冷清清,却也付出了许多的艰辛。像是他在《今天,我被红孩的散文灌醉了》中写道:“这些年,因要顾及衣食,不敢认文学为父母,便如做贼一般偷偷地爱着,总嫌身不得自由,思不得张扬,窝在散文的井底,找不到归家的路径。”当然我们也希望,益鹏在文学的道路上,不要再“如做贼一般偷偷地爱着”,希望他更快地找到回家的路。
以笔为杖相扶将
一个对文学抱着如此热情的人,文学至于它的意义就不限于打发时光这么简单,应该说更多地是他精神的支柱,也是伴随他远行的手杖。他在记叙叶广岑说道:“我把她获奖的这个消息在手机里收藏起来。再过十年、二十年,它或许可以给我当拐杖。”这样的信念应该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埋藏在了心底。他在《我的金融文学梦》中这样说:“山大,地僻,人稀,又不通班车。那的确不是一个能拴心留人的好地方。许多年轻人,但凡有点门路的,都不会去那里谋生。好在,高中时期,我就喜爱上了文学,渴望找到如北大荒之于梁晓声那样的‘一片神奇的土地’。在此后的日子里,文学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文学,陪伴我一起走过了那段坑洼不平的道路。” 这表明文学的的确确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依靠。
益鹏将文学作为自己人生的一种依靠,而这种依靠又常常表现为与文学同道在心灵和精神上的相互扶持。他在《扶贫,一个庄严的命题——杨志勇〈追寻初心——我的扶贫札记〉读后》写道:“细细品味其中88篇札记,皆是充满田野芬芳、草木本心和人生智慧的优美散文,既可见扶贫工作者的鲜亮初心、艰辛努力、顽强拼搏和丰盈的生命体验,亦可特别感受到乡亲的奋斗、幸福和快乐,还有乡村的变迁、美丽和忧伤。” 更是在文中直接发出感叹“在微信中,我对志勇说:好羡慕你!”可以看出益鹏的文学本心、淑世情怀。无独有偶,他对于与自己一起在文学道路上奋斗的同道总是怀着深切的眷恋和希冀,像是他在《一片冰心在玉壶》中写到了同为陕南的三位女作家:“她们都生长在秦巴山中,但却没有为其所困。王晓云当初毅然决然走向大上海,杜文娟义无反顾走向青藏高原,都走出了一片属于她们自己的新天地。徐祯霞不是靠身体出走,而是靠思想远行,让文字驮着她的聪明才智,突破秦岭的层层禁锢,飞向天南海北。” 某种意义上,益鹏将这些同乡文友的文学实践,作为了自己文学理想的一种延伸。
或许是文人多敏感,对于益鹏之所以投身于文学评论的事业,我总感觉与我有些关系。他在陕西金融作协担任丝路金融文学网站的常务副主编,一直催促我为大家写些评论,我虽然满口答应,但是总是口惠而实不至,实在是对各位同仁情谊有亏,于是益鹏就开始主动承担起这个工作。这本集子中就收了他评论陕西金融作协杨军、赵小舟、吴文茹、大唐飞花等人的作品。你一看这些文章便能明白,益鹏在这上面的确是费了很多的心血,其中对于吴文茹、大唐飞花诗歌所做的评述,写得尤其出彩,显示出了很强的文学感悟能力以及扎实地文学理论功底。虽然我通过益鹏的文字来把握这些同仁写作的精髓,有点像柏拉图所说的,与真理隔了三层,但我的确通过益鹏的写作,在这些同仁的创作中发现了很多难能可贵的个人体会。
仔细体会益鹏的诸多评论文字,虽然在《晓蕾的人与文》一文中,他说:“一个成熟的作家,不仅要熟稔写作技巧,更要精通从生活中撷取创作素材、提炼艺术精华的技巧。而这两个技巧,恰恰都是我的弱项。”但实际上他的一些议论堪称高妙,读罢,使人顿生“吾不如也”之感,像是在《碑林诗人的精彩亮相》一文中,他说:“当诗歌被迫置身于一个广大、混乱的消费现场,她是否还需要坚守自我的精神边界?她的终极使命是否还是为了探究心灵、解释存在?至少,在某些诗人的内心,仍一直对诗歌心存这样的执着。因为他们坚信,一个强调写作的存在性和精神性的淡定而从容的诗人,不会哀怨,不会彷徨,无论当下的生活或世界是多么寂寞多么无奈,其创作仍然犹如心灵里一种隐秘的念想,一根了解自身存在境遇的细小管道,在书写中为我们坚持不懈地贡献着一种对现实、对时代、对世界的精神担当和文化引领。” 这样的论述,诗歌的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有机统一,一般属性与个人体验相互融合,的确是体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准。
一些浅陋的建议
前面谈了从益鹏的作品中所得到的各种体悟,但在此同时,为他对文学的热忱所感动,我实际上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带着批判和挑剔的态度在阅读,希望真正发现他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能够助他早日抵达自己的文学之境。平日里,益鹏是催我写东西最积极的一个人,我也应该用这样的真诚来回报于他。实际上在阅读整个文集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益鹏的这种文字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文字有着比较扎实的功底,时不时的还透露出文人的情怀和情趣,文字上的感觉也细致入微,有了这些基础,再加上他与生俱来的现实感和使命感,应该说有了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条件,或者产出崭新审美体验文字的基础。但这样的要求可能太高了,用一个大作家的标准来要求益鹏,可能有些勉为其难,虽然他心中所怀揣着文学梦想要求我这样来做。
讨论益鹏的文字之所以与文学之境还存在着一段距离,我想首先还应归咎于益鹏以及与他一样热爱写作的人,他们的写作时不时的总会表现出一些公文的特点,总会透露出一些宣传的习惯和口气。对于这样的文体风格的来源,当然应该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来找。这种宣传文风的形成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基础,在诗歌上像是李瑛、郭小川、公刘等人的现实主义诗歌,再加上我们曾经对于现实主义风格又做出了过于片面的理解,后来各种现代主义尝试着对这种文风进行改变,但在社会层面上其实收效不是很大。对这些文体风格我当然不会有什么偏见。人类文学史尤其是现代文学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崭新表达方式的过程,所以也为各种写作风格和方式都留下空间。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民间化、民族化,不是口语化、材料化和直观化。更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写作者不能总在狭小的文学视野里打转。对于人类丰富的内心活动,甚至是原始欲望,要能勇敢的面对,对于各种角度以及风格的尝试,要能以宽容之心来待之。
而在我看来,益鹏的一些论述,在铺张扬厉的文风推动下,有时显得过于严厉。像他在《关于诗歌,抗疫期间的另一种“热闹”》写到:“诗歌本身没有错,错在诗人,是诗人没有把握好诗的方向,以为诗是一个大菜缸,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以为诗是红灯区的婊子,谁都可以扑上去,想怎么凌辱就怎么凌辱,没有谁管得着;以为诗不需要用良心去称量,只要耍耍机灵、玩玩技巧、能博得众人喝采就好。如此对待诗歌,实为倒行逆施,舍本求末,自然与要到达的目标相去甚远。技不如人,可以调理,如良心癌变,就无可救药了。如若真走到那一步,诗歌离沦陷与消亡也就不远了。” 这样的表达的确酣畅淋漓义正词严,可以说也切中了一些时弊。但这样的力道猛则猛矣,却给人以口含天宪之感。从现当代文学史来看,这样的批判风格对于文学发展不仅推动有限,相反还会成为一种桎梏。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长时间里所形成的评论风尚,实际上把文字当作了一种思想认识的工具,一种道德教化的工具,而将文学的审美和形式放在了第二位,长此以往,反过来又会损害了文学本身的认识功能。别林斯基所倡导的审美的历史的评论原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相反。这也要求我们在写作评论时,也要重视自己的情思,尊重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更加关注其形式上的创造性,这才能够为文学创作提供一个合适的空间。再一个,益鹏的一些结论还存在一些可议之处。像是他在《拜见陕西文坛的另一座山》中说:“如果说《平凡的世界》的作者是两眼向下,面对泥土,沉陷于繁琐的世俗生活不能自拔,那么,《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给我的感觉则是飞翔于天空,以鹰一般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社会和人生。”应该说这样的评价与《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存在一定的出入,在现实主义概念下对于小说本身的风格特色存在一些想当然的认识,这实际上低估了文学理论、文学作品的复杂性。当然,益鹏这样的认识也算是他个人的体会,他拥有这样评判的自由。与此同时,我们也相信,益鹏通过不断的对比辨析一定能够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达到更高的境界。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浅近的看法。我从益鹏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需要更加努力,因为有益鹏这样喜欢文学热爱文学的人激励着我,我没有理由停步不前。当然我们向不以自己所是为人间唯一所是。对于益鹏文字所写下的这些感受,可能就像是杜甫所看到的那隔叶的黄鹂一样,只是于碧草繁盛的春色中发出一些声微却不乏价值的鸣叫。但在这个网络文学大繁荣的时代,我们需要各种文字声音发出来,即使现在这些声音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因为其基数庞大,保不齐在如此广泛的基础上能脱颖而出几个不世出的天才,那么说不定一个真正文学的新时代也就到来了。对于益鹏以上所写的这些文字,对于我这里喋喋不休所写下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从这样的视角来视之。在这个时代,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可以尝试,这符合文学自由创造的本质属性。当然重要的是在写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各种的意见,从而在提升自身的基础上,也同时提升社会的审美认识和历史认识。应该说我的这些看法实际上有很多是在益鹏的感染之下做出的,在一种情绪的激励下也学着益鹏做了一些直抒胸臆的评论,也因此这些评述还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不周之处,还请益鹏宽容。
(姚明今,博士,中文系副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影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本期责编: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