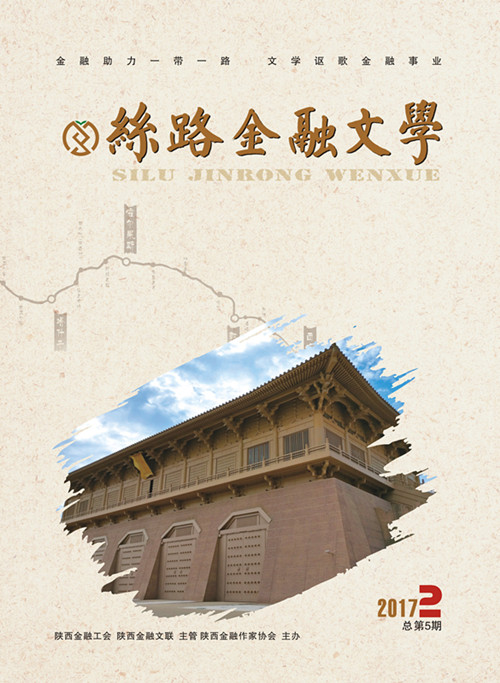一
生于上世纪五十、六十或七十年代的人,大约都有一种对首都北京无限崇敬,或者说敬仰的情怀。姑且我就把这样一种情怀称之为北京情结吧。
我生于1973年,所以记事以后,我也无法避免地拥有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白,对北京既敬畏又向往的情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情结呢?我想无外乎有两个原因:一是那个时代对伟人、对领袖人物近乎神化的一种狂热崇拜,所以爱屋及乌,继而对伟人和领袖的所在地也开始产生一种摩拜的思想。二是因为教育的导向,让我们不由自主,或者说不得不,开始对北京产生了无限憧憬,既敬重而又敬畏的复杂心理。
记得,还是刚上小学的时候吧,《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成为我入学以后学会的第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在当时被要求,每天上课前都要唱。除此以外,收音机里每天的新闻,报纸上的消息,基本大半以上的内容都跟北京有关。这就等于我们在时刻被提醒憧憬着,在一片蓝天下,红旗飘飘的天安门景象。因而,在那个年代,首都北京在我们的生活中,简直就是一个神仙殿堂般的存在。
这种崇拜,在我学习了小学课文《库尔班大叔上北京》后,达到了极致。
库尔班大叔原名库尔班.吐鲁木,是和田地区于田县农民。他从小失去父母,在地主巴依家的羊圈里度过童年。为挣脱被奴役的生活,他带着妻子逃到荒漠里,靠吃野果生存。后来,在地主巴依的迫害下,他妻离子散,独自度过了17年的野人生活。新疆和平解放后,库尔班大叔知道,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救了他,使他翻身解放,回到人间,过上了幸福生活,便执意要到北京去见恩人毛主席。就这样,库尔班老人背着馕袋,骑着小毛驴上路了。历经坎坷,1958年6月28日下午,75岁的库尔班大叔同其他全国劳动模范一起喜气洋洋地来到北京中南海,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这个故事后来继收入小学课本后,又被改编成了歌曲、电影等不同的艺术形式问世。当时,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新疆,而且就在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所以一度成为我们引以为豪的标榜,也更加激发了我们对北京的向往。
对北京超乎寻常的崇拜,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曾经伴随我很多年,在我逐渐长大成人之后,虽然有所消退,但这种情怀却已经根深蒂固。在老百姓的眼里,北京那就是皇城,是一个威严而神圣的所在。所以,北京城在心目中的地位绝对至高无上,不容小视。
二
这样的敬仰情结,大约到了2008年,在听了来自北京的歌手汪峰演唱的歌曲《北京,北京》后,第一次受到了冲击,内心开始有些疑惑起来。
“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歌手沧桑嘶哑的声音以及阴阳顿挫的曲调,形成强烈的对比。咖啡馆和霓虹灯的对应,广场和月亮的碰撞,而挣扎,告慰,拥抱和碎梦,这样的语言,应该是有着深切成长烙印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欢笑对哭泣,活着对死去,为了迷茫的心而祈祷,为了失去的至珍而寻找。感觉歌曲就是在压抑中,寻找宣泄的突破口。无法想象,这竟然是一首倾诉北京的歌曲。在这里,请原谅我的断章取义,因为这样的伤感,与我心目中的北京城实在是格格不入。
这种疑惑,后来在看了一场电影后,得以释然。
其实,我不常看电影。最近一次上电影院看电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也许是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儿》,有着太多老北京的故事,所以,带着对我所仰慕的北京,窥探一二的想法,我在电脑上观看了这部电影。“老炮儿”是北京人对那些成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的称呼。冯小刚饰演的老炮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但他做的又是些帮人打抱不平的很没意思的事情,但这些没意思的事透着朴素的人性。他对他那帮老兄弟的义气和维护,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性。而最后,用江湖的办法来解决现实中的现代恩怨,虽然有些悲壮的意味,但也昭示着老北京人性格当中的那种侠义情怀,已经完全落伍,消散在了历史的洪流中。
虽然《老炮儿》对于解答我对北京的疑惑,也许有些牵强。但是在看完电影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已经固化的北京情结,虽不至于轰然坍塌,却也真实回归了理性。北京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顺应了它,它可能是天堂。不顺应,它也可能是地狱。
三
在我过完四十六周岁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遗憾,或者说是一个缺憾。尤其是在我的内心里,还有一个北京情结的情况下。不过,人这一辈子,遗憾的事总是会伴随左右,就像苏轼在他的词《明月几时有》里写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不过,这个缺憾在我即将渡过我四十六岁生日的时候,在惶恐中被弥补了。经陕西省金融作家协会推荐,我受邀参加了2019年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的文学培训班。
其实,这许多年来我有不少的机会,可以去北京走走看看的。而且,我的大姐就常年居于北京。但是数年来,我利用假期游历走过了许多地方,却独独没有踏足北京。这是因为在我内心里,北京已经成为我心中的一道坎。
这种感觉既像是一种敬畏,又像是小媳妇怕见公婆的羞怯。于是,既然与北京的相触有这样的压力,那么干脆也就不要去好了。我知道,这一切矛盾的根源,还是来自于我一直以来的那个北京情结。
临行前,在微微地惶恐里,我静坐在咸阳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的座椅上,麻木地看着窗外。一架架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繁忙地此起彼落。大约再有一个小时后,窗外一架编号为MU2107的飞机,就将载着我从这里起飞,然后再三个小时后,降落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时刻,我却没有多少兴奋或是期待,只有一些莫名的羞怯与担忧。这个羞怯和担忧除了有对文学的不自信,还有对即将面见北京的紧张。
也许是与此刻惶恐的心情很有几分相似,此刻,我竟然又想起了已故著名作家高晓声先生,笔下的一个人物——陈焕生。《陈焕生进城》这部电影,是从我记事起,看过而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部电影。大约是在1983年左右,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看的。后来在乌市上学后,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又专门看了原著。
小说中的“漏斗户”陈焕生,日子过得好了后,就想着进城里去卖麻花,做点小生意,给自己买一顶帽子。而主人公初到城里那种怯生生的描写,和陈焕生第一次花了五元钱,住进铺有雪白床单的招待所,害怕弄脏了床单那种胆怯的情节,与我对几个小时后,即将到达北京而感到的恐惶,有如出一辙神似。想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四
老北京的文化起源于元朝。那曲折幽深的小小胡同、温馨恬静的四合院,是如今的北京城里保存不多的,还带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古老的传统特色、浓郁文化气息的遗产。相比起北京城四环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些遗产正在消失和被遗忘。
不过,又是一个遗憾,中国金融作协安排的培训地点,选在了距离首都机场不太远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交流中心。培训安排的还非常紧凑,连夜晚的时间都没有放过。这也预示着我将与北京城里曲折幽深的胡同、温馨恬静的四合院失之交臂。
两天紧张的培训,很快结束。与这些从全国汇聚来的金融文学大家们相比,感觉自己始终还未能进得文学的这道门坎来。所以,在那天晚上的诗歌朗诵会上,我借故早早地离开了。一是因为这样高规格的文学盛宴,以我的文学素养,还未能达到消受的层级。二来,就这样结束与北京的第一次接触,我还是有些于心不甘。于是,就想离开酒店出去走走。
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交流中心坐落的位置,已是北京城外的郊区。走出酒店后,道路两旁都是一些仿四合院的别墅建筑群。但是除了道路两旁的路灯以外,整个别墅群基本沉寂在黑暗中,少有几处亮着灯火的。这样的沉寂,让人稍稍有些恐惧。走过几条街后,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小集市,但也是稀稀拉拉没有几个人。这时,一阵阵的寒风,已让我无心再走下去。
回去的路上,我好奇地想仔细看看这些仿四合院建筑的别墅。走到一座宅院的仿古门前,刚准备扒着门缝看看里面的格局,忽然一条恶犬在里面狂叫起来,吓得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离开了,生怕被别人当成了窃贼,而难辨清白。转念一想,这样荒寂的街道,估计也没有人来,不过是自己吓自己罢了。
离开北京这天,是个阴天。收拾行李的当口,我联系了滴滴。才走出酒店的大门,滴滴司机就已经赶到了门口,并帮我拎起了行李箱。这样周到的服务,让我忽然有些小小的感动。于是,在车上,我与司机聊了起来。
“你来的好快!”我赞叹道。
“嗯,我就住这附近,看到滴滴信息就过来了。”司机小伙看起来有些腼腆。
“你是北京人吗?”听着口音有些软糯,我不由得问。
“我是安徽人。跑滴滴的,基本没有北京人。这里当地人,土地被征收后,家家都有近千万的补偿,谁还出来赚这个下苦钱。”说完他苦笑了一下。“我在城里面工作,但这里的房租便宜些,今天是我轮休,所以出来跑一跑滴滴。”
“哦,这么拼啊”
“哎,不拼没有办法,在北京随便一套房都得大几百万呢。”
“嗯,确实挺难的,为什么不回老家安徽找个事干呢?”
听完问话,司机小伙子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抿了一下嘴唇,不再说话。
在北京返回西安的飞机上,我睡着了,似乎梦见我又回到了小的时候,在一间小小的教室里,我和同学们在高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随着飞机最后落地的颠簸加剧,我才醒了过来,这两天的培训真得好累!走出咸阳机场大楼,竟然是个晴天,突然感觉心情无比的轻松起来。
[责任编辑 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