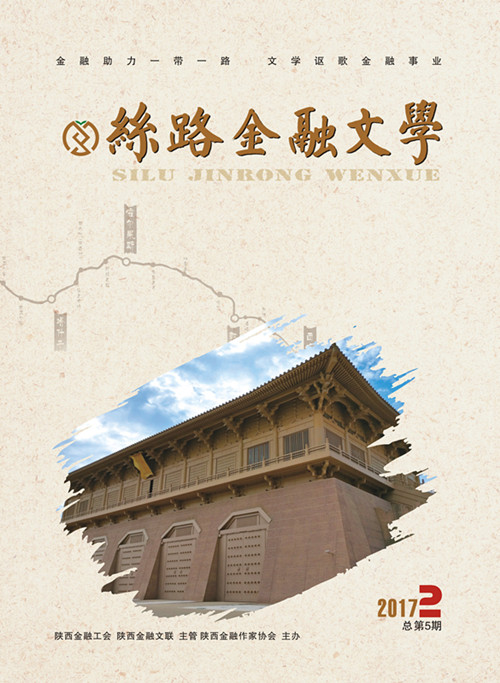一
二十年前,父亲带领我们举家返回故乡。与往时返乡探亲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一家从此要在“故乡”的土地常住下来。
事实上,在我童年成长的记忆里,返乡探亲的机会很少,所了解的自然不多。父亲幼年丧父,少小便离家外出讨生活,到黔桂交界的一座矿山挖煤三十余年。待到年老体衰、力不从心的年岁,却赶上矿山破产倒闭,加之父亲生性本分,怀揣“落叶归根”的世俗观念,决定拖家带口返乡当农民。
在我成长的记忆里,“故乡”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我的童年一直是在矿山度过的。在那里,我经历了人生最初的启蒙和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父亲是一名煤矿掘进工人,亲历过无数次井下透水、塌方、瓦斯泄漏等险情,幸而他每一次都侥幸逃离险境,得以平安归来。
事实上,父亲的故乡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雅楼”。听起来,像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其实不过是当地的土语音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壮乡山寨。而壮话是当地通行的官方语言。因我至今不通壮话,所以对这个有着好听名字的故乡,始终有着某种抗拒的愁绪,如果不是父母健在,并且在此定居多年,恐怕我一辈子也不会踏足这个山高路远、地少人多的偏僻乡村。
然而父亲的返乡之路,并没有预想般顺畅。在他外出务工的几十年间,原来名下的责任地早已划归生产队所有。返乡之后,父亲即向村部申请划拨耕地,遭到了生产队的回绝,理由是父亲一辈原本由外村迁居而来,非本村原住民,加上族上亲戚疏离,势单力薄,数次申述无果。谨小慎微的父亲,担心因此招来是非,今后更难以在村中立足,几番思虑之后,只得放弃。
而我的母亲,则是另一个县份的城镇户口,我们兄弟二人随父亲在矿区长大,入的是“农转非”户籍,村人猜测父亲领了巨额养老金回乡享福,亲戚则顾虑父亲回乡争夺自家名下不多的土地,因而屡受排挤。父母苦于生存压力,以及我们兄弟二人的学杂费,只得拿出半生积蓄买下村里的一块田地维持生计。而我则转入当地的乡村中学就读,因为语言的隔阂,常常受到本地学生欺负。对于故乡的怀恋,感受到的并非是乡情的温暖,更多的是由心而生的人情冷淡。
回到故乡,四顾茫然,心生彷徨。这里没有我成长的印记,没有熟悉的山岗、玩伴,甚至我的生活、语言都与之格格不入,一张嘴便显露了生分。那时候,我们全家人借住在村边的一栋老旧的木楼里。木楼不大,因为常年空着,便成了临时堆放稻垛的柴房。我的小床就摆放在稻垛边上。每到秋夜,稻垛里常有虫子在鸣叫,时常把我从梦境中唤醒。秋夜薄凉,我透过木楼瓦楞的裂缝,看到明月高悬,月光滴落脸上,耳畔风吹竹动,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袭遍全身。刹那间,我的泪水奔涌而出,一种无法言说的乡愁之痛,变得真切可触。
在那个月光凄迷的故乡的秋夜,我就着窗前的明月写下生平第一首诗。从此,我的心头燃亮一盏灯火,点亮孤独也照亮了寂寞。我开始拼命地写,写心中的渴望和向往,写另一个故乡和村庄,以及内心一闪而过的风景。我不清楚段落和句式的区别,也不明白诗歌是一种怎样的体裁。只隐约感知到,一些文字段落分行之后,会呈现另外一种不同的效果,更轻易贴近心魄,激荡灵魂。语言的非凡魅力,令我禁不住兴奋,让我茫然无措的内心变得安静。我开始写那些分行的文字,捕捉内心的花火,把心中的苦闷、惆怅,汇聚笔端,写入纸片……
所幸一年之后,我便从那所乡村中学毕业到外地求学,而后一直在外工作和生活,时光荏苒,转瞬已逾十数年之久。而令我始终怀念的故乡,早已在我遥远的怀乡梦中分崩离析。因我从小在矿区长大,所有成长记忆都与矿山有关,所怀念的人与事,早已随着矿山的倒闭烟消云散,数万矿工子弟为寻出路,散落天涯,自此离去,便永难相见。而父亲的“故乡”没有我成长的印记,没有熟悉的山岗、玩伴,甚至生活、语言都与之格格不入,一张嘴,便显露了生分。
而今,我早已没有了故乡。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揣度父亲当年是怀着怎样一种内心的挣扎离开故土?而经年之后,又是怀着怎样一种渴望返乡?
当我回到老家,面对这样一位满头白发、口齿笨拙,被他乡放逐,又被故乡拒之门外的老矿工,在他心中深藏着一种怎样的痛楚与悲伤?往事如尘埃落定,一切化作过眼烟云,如今已年逾六旬的父亲喜欢长坐在家中的竹椅上,眼睑低垂,常常让我以为他睡着了。不经意间,父亲会从嘴边吐出一段话,抑或几个熟悉陌生的名字,让我心头微微一颤。我猛然顿悟,晚年的父亲是在缅怀他漫长的一生,在乡愁的深渊,缅怀另一个远逝的“故乡”,这便是父亲有生之年的“怀乡之痛”。
每当这时,我所能做的便是陪伴在侧,细致聆听父亲昏沉的呓语,满含热泪,却欲哭无声……
经年之后,我也已在外娶妻生子,怀揣“还乡梦”混迹在城市的丛林忙活。当我浪迹异乡,抑或穿行在城市的人群中,我依然感到孤独,唯有文字喂养乡愁,疗治魂灵,保持一份内心的鲜活,感知人世悲喜与世事变幻。
暮色的幽冥中,一种静穆的错觉在四周漫开。那些缓慢的、泛着青灰色光芒的夜色笼罩我的全身,溢满我的房间。我习惯在这样的氛围里书写,那些浅淡、幽暗,沾染夜色的诗行,与我内心弥漫的色彩非常接近。我始终坚信,诗意始终是心灵透过的一束光,洞彻心扉,更是一种内心的坚守和向往。
二
那些老旧的青石板、土坯房、青石堆垒的栈道、泥墙斑驳的屋檐还在。小径通幽,溪水潺潺有声,淌过幽林密谷,田畴在金灿灿的阳光下静静变黄。此时的村落空寂无人,霞光中,几分凄清、几分落寞,仿佛稀时的老人独对夕阳,思虑万千……我沿着河堤一路徜徉,一面观瞻城郭旧貌换新颜的妆容,一面细致聆听它沉静如迷的呼吸。事实上,大化县城建制不算悠久,却也颇有些年月,自有其深入纹理的故事与往事。而红水河两岸,楼宇鳞次、民舍栉比,河堤板路光洁透亮,一路伸延,遥向更辽阔无垠的山野谷地。一如这座山间小城,四面峰丛环绕,亘古的红水河穿城而过,流水汤汤,终年端急,幽悠鸣唱,仿佛母亲的耳语,轻声召唤着万千游子梦归故乡。
乡民临水而居,村庄依山而建。流水,遇沟而过,绕山低流。那些流淌在山间的岁月烂漫无声,时光只惊人的一瞥,便将山村的晨昏点亮。曾经,我幻想在这片澄净的天空下,结庐为舍,手执书卷、赏风颂月、观流云舒卷,远避喧嚣于尘世,如同父辈,过人世间最节俭的生活,直到静静终老在清风绿水间。
如今,行走在苍茫山道上,人烟寥落的村庄少了些许烟火气息,想昔日鸡犬相闻,炊烟四起的农家景象,都已沉没在过往岁月中。曾经走过的路,看过的云,全都悄然隐匿,不知所踪。然而,少年时的旧居还在,房前屋后,窗台院落,四处散落着童年的碎片。伸出手,推开故居颓朽的门,旧年影像依然清晰可辨,一切近在咫尺,又如此寂寞遥远。所有成长的记忆,无论快乐抑或忧伤,都沉落在心灵的底片上,凝固为石,风干成内心的影像,凭靠记忆温暖擦拭,直到透射出别样的光和亮。
多少年了,我仿佛从未仔细端详过这片静默在山野间的茅屋草舍,也许山村每天都存在,即便这个村庄隐匿了,那个村庄还在。只不过,村东和村西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关于村庄的记忆已然与水融合,无法辨认出消失的是哪一个村庄。
无声的水,渐渐淹没了村庄。那些曾经走过的村落、房舍和小路,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同时消失的,还有田畴和炊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现如今,眼前取而代之的是一湾碧水,如绸似带,浩浩荡荡,拂过驻足者的视野。抬首,目力所及之处,偶见裸露的树冠和悬挂的渔网,几只灰头土脸的水鸟栖落其上,偶尔拍落几声幽鸣,亦随远道而来的清风遁入空茫。
世事沧桑,山村的每一缕风、每一轮新月,都将定格成生命中永不消逝的风景。时光飞升如炊烟消散,当岁月载着村庄渐渐远去时,昨日所有的梦恍如隔世,曾经努力寻访的痕迹已然无迹可寻。我知道,村庄终会被水带走,最后消逝在一湾碧水之中……
哦,我的村庄消失了。人,许多时候是怀旧的。一棵树,一束花,一株草,便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便有无数心事在心中搁浅,繁华过后,化为烟尘,沉落在心,永不消逝。
如今,离开故乡多年,对于故乡的怀念,如同蔓生的杂草,却在心底日显蓬勃了。
现在,我站在高高的观景台上,放眼眺望故乡,眼前却是一片迷茫。我不确定自己要找寻些什么,虽然我知道我所有的努力,终将是一种徒劳。但是我并不甘心,我心底依然记得那些故乡的事物,一如芳香的稻垛、闪亮的炉膛,微微透出烟火的味道。如今,我像一个孩童,在流光溢彩的俗世里走失,以致找不到回家的路……
面对故乡,我永远是个沉湎在成长记忆里的孩童。从故乡到异乡,又有谁对于成长的记忆不留痕迹呢?当我再一次回到故乡,寻访一些被时间洗过的痕迹,那些曾经一同追逐、嬉戏的孩子,仿佛还没洗净手掌上的泥巴,不经意间已成为了人夫人妇。而那些慈爱的老人,在不确定的时间走向泥土,长眠在村边小河旁,垒起来一座座土丘,仿佛一道道生命的站台。而数年前,那儿曾是我们游泳后晾晒衣服的地方……
我每次返乡,都会选择一间僻静的屋子闲住几日。待到赶圩场的日子,便可买到当地人自己出产的土物,比如棉鞋或者草编的鞋垫一类的小饰品,做工精湛、漂亮而实用。在我们村上,每户人家房前屋后都种有一片小竹林,或生长着几株苦楝树。眼下这个时节,树的枝叶已经繁茂得很,轻风拂过时,叶子的沙沙声便响成一片。每当这时,总会引来几声警觉的犬吠,衬托出村庄无比的安宁和寂静。老宅院前的空地上,一方石磨墩坐在地,缝隙间满是青苔。此刻,上方站立着一只黄犬,正伸长脖子,朝向山边的落日放声狂吠,顽强而固执。
吠声袅袅。落日时分,黄犬的吠声总是让我心生感慨。我知道,它的叫声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寂寞。那犬吠声明快而悠远,如同一支黄昏的恋曲。而那落日,在黄犬的召唤下摇摇欲坠,向着山涧徐徐沉落……傍晚时分,我常常独自到村边走走,脚上踏着薄露,听远处村子传来声声犬吠。我甚至这么认为,寂静的村庄因为有了犬吠声才显得安宁,村庄的夜晚才如此静穆、祥和。薄暮里,烟火的气息在我们四周弥漫,一串细微的咳嗽声,隔着木门,在炉膛深处闪亮,回忆里透着土香,是童年的味道,仿佛我们从前的故家。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往事徘徊不去,那些洋溢在心间的念想,静默到无声。吃过晚饭,村民们不约而同地围着火塘交谈。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神情都是凝重的,他们在想今年的收成或农事,偶尔会提及一些过去年月的人和事。火塘里不时爆出阵阵轻微的“噼啪”声,蹿起的火苗星子舔着柴禾,将火光映照在众人的脸颊上,光影分明。
暮眼昏沉的老人吧嗒吧嗒吐着烟圈,低声说着话。晚生则端坐在近旁,神情庄重。一些老旧的故事经由老人沉郁的语调传递开来,便都有了宿命的味道,如同火塘里蹿出的袅袅烟火,总是熏得人们泪眼酸痛。平日里,如果村中哪家来了客人,往往没等到主人跨出门去,那犬的吠声早已迎出门去,它摇晃着尾巴,跑在主人前头,为主人迎回来访的客人。转入厅堂,木桌子上菜肴齐备,自酿的土酒醇香溢满,那份豪情和酒盅总是盛得满满。
若是在深夜,那河岸有人连夜赶渡,手上握着灯笼或者手电筒,只要隔着宽阔的河面轻轻摇晃一下,便可听到沿岸传来“汪”的一声犬吠。不多时,河那边悠然地点亮一盏如豆灯火,一个佝偻的背影摸索着来到河边。“哗啦啦”,一阵清脆的渡船链锁声从水面传来。至今,那清越的声响还在小小的渡船上颤悠着……
告别村庄多年,我像一只鸟在城市的狭缝里觅食。那些被楼群分割得有棱有角的天空,让我感到惶恐和迷惑。站在这座城市的高高的额头上,我拉长目光远眺故乡,那些堆得高高的柴火、稻垛、泥墙黑瓦,以及黄昏时分黄犬迎接落日的声声吠叫,正将一个“异乡人”瞳孔里的苍茫放大。
三
搭乘的巴士在熟悉又陌生的乡道间行驶,透明的光线中,三月的风拂在脸上,依然感到丝丝凛冽。我抬眼望向窗外,远处一闪而过的房舍、桑田、谷地、错落搭叠的峰丛、林莽,以及不远处村间小路上欢快奔跑的孩童,瞬间使我心头掠过几分久违的感动。
短暂的路程中,一阵不期而至的细雨洒落车窗,眼前扬起了雾气,玻璃窗上映现出一张模糊的脸庞,使我陷入一阵恍惚,仿佛又回到了孩堤时代……
回望十数年前,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曾在这片熟悉的山水间裸足奔跑。这里的山野谷地、废弃的路轨,甚至此刻头顶上升腾的雨雾、路旁桑田散发的田园气息,我都熟悉,都感到亲近。我固执地认为,一个人的出生地,与一个人心灵和情感的成长始终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也许,每个游子心中都埋藏着这样一道温暖的疤痕,而那方生养的土地、熟悉的山岗、流水,在漫长的岁月中,会慢慢生长成为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
道路无尽延伸,记忆却驻足不前。我陷落在记忆的围城之中,往事犹似默片闪现,一种丧失家园的隐痛,在脑海中变得清晰可触。巴士仍在乡道间一路疾驰,同行的诗人那超突然向我召唤,他指给我矿工安置区所处的位置,沿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向窗外,车窗外是一排排矿区易地安置房分立路旁,只觉住宅区人迹寥落,一些杂草蔓爬上路基,似乎已经许久没人前来打理。微风过处,几簇茅丛随风摇曳,约略可知安置区的荒凉与寂寥,心头不觉略过一丝感伤。而道路的另一旁,两条锈迹斑驳的荒弃路轨,塌陷在一根根腐朽的枕木上,横贯于通行的公路上,如同一根骨刺横穿腹体,让人感到有种如芒在背,浑身不自在。
曾经,这里也曾热闹非凡,无尽伸延的路轨上终日疾驰着运载火车,日夜不息地将矿区生产的上等无烟煤输送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同时也搭载着矿区子弟驶向外面的大千世界,捎回外界的信息。其实,早在四、五年前,我就曾慕名来到小镇探访儿时旧友,只是搭乘的已不是运煤的火车。
遗憾的是,那一次洛阳之行,在镇上仅遇到两位在留守务工的同学,更多同学早已外出打工,甚至已经多年没有再回来。我们在路边破旧小店里小聚,谈起了曾经的过往,以及这些年来的人生际遇,知道矿区倒闭后,许多留守的矿工子弟他们的生活并不如意,言谈中难免生出几分拘谨与生分,心头不禁唏嘘,曾经各自脸庞上洋溢的那份天真浪漫,早以被现实中的困苦生活消磨殆尽。
随我一同前来的是一名小学同学,她们一家早在1997年就已离开矿山返回故乡。而后的许多年,我们便失散了,从此杳无音信。然而,我却时常会想念她,那会也就是十三四岁的年纪。那会儿,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耍,上下学一起走山路回家。沿途,我们说着别人的闲话,她的笑声清澈响亮,仿佛山野间晃动的风铃,眼睛里闪动着透明的阳光。那些流淌在身旁的时光像流水一般蔓延,于是岁月便显得极漫长。我们常常独流浪在山野间,野野地长着,却仿佛永远也不会长大,如此便时常让我们陷入对未来的焦虑,感觉成长许多时候是一件顶无趣的事情。
然而,时光还没来得及等到我们长大,她便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第一次,让我有种掉了魂的感觉。这种感觉,直到经年以后,依然真切,依然泾渭分明,仿佛指痕掐在肉里,生生的痛。如果一直像从前,如果一直没有长大,那份牵挂与念想,也许就能永远停留在青春岁月,那该有多美好?
这种疼痛太深刻,也很透彻,纯净如流水,始终藏在心底,大概永远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这份情感一直深埋在心,至今想来,仍觉不可思议。
上世纪80年代,我的父亲随同第一批矿工来到矿区当矿工,被分配到煤炭掘进队,驻地位于黔桂交界。而后,我在矿区出生,一直长到十多岁,可以说我的童年时光和最初的人生启蒙都是在矿区度过的。直到1997年末的某一天,走出矿洞的父亲接到了矿山濒临倒闭的通知,矿区的生活便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而接下,便是漫长的等待和无尽的抗争、大规模的上访、维稳,甚至是械斗。最终,在盛大的维稳镇压下,数万名矿工不得不接受现实,被迫妥协,选择分流安置,或者遣散返乡,其中一部分不愿返乡的矿工留了下来,成长为新一代的环江人,他们被当地政府集中安置在洛阳镇安置区内,没有土地,依靠微薄的生活保障金度日,间或依靠经营各种小本生意,或打零散工艰难维持着生计。
更多矿工子弟则淹没在那场盛大的南下广东的淘金洪流之中,尽管生活依然艰难困苦,好在总算有了一处安身立命之地。而另外大部分矿工,如同我的父亲,则拖家带口返回各自的故乡,重拾过去的生活。只是回不去的是时间,老去的亦是时间。他们从青年出发,转身已是暮年,仿佛生命又回到了起点。只是,返乡之后的父亲早已丧失了土地,并未能遂己所愿重新做回农民。而乡人们则猜测他在外闯荡的几十年,积攒了大笔钱财,如今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得享清福。父亲百口莫辩,几番唇舌下来,顿觉无趣,从此寡言。
直到现在,我仍无法揣度父亲当年是怀着怎样一种内心的挣扎离开故乡,而经年之后,又是怀着怎样一种渴望重回故乡。
而如同我辈,那些无处安放的青春,却再也回不去了。我们丢失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故乡。而我的故乡,早已在那场浩大的下岗大潮中分崩离析,云烟散去之后,剩下的是满目疮痍和内心隐忍的创痛。温暖的记忆总在梦境的那一边,回不去,也走不到,一种无法言说的怀乡之痛,从来都是真真切切,不可触碰,却又始终挥之不去。
一直以来,我对环江的感情,内心深处始终有着某种无法言说无法释怀的情感。尽管当地交通闭塞,物资匮乏,那些缓慢的时光、透明的蓝天、流浪的白云,却有着令人难忘的静穆时光和天地天籁。我的记忆深处,依然浮荡着那些熟悉的事物,一如芳香的稻垛、闪亮的炉膛,透出微微烟火的味道。……那些旧年影像清晰可辨,仿佛近在咫尺,又如此遥不可及。所有成长的印记,快乐抑或忧伤,都沉落在心灵底片上,凝固为石,风干成心中的暗影,任凭记忆温暖擦拭,直到透射出别样的光和亮……
如今,时光转瞬已是十数年光景,当我走在暗影丛生的霓虹灯下,或者穿梭在奔忙的人群中,我时常感到孤单。我知道,那些缓慢的光阴也会消磨掉我们脸上的青春,包括那些沉浸在时光中的事与物,也将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隐遁到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当夜色四起。远处山顶上的灯塔透射出微暗的光,将城市的喧嚣与沉闷稀释到有限的高度。在冷酷与静穆并存的夜晚,现代建筑又将城市的夜色切割成有棱角的静默。透过稀薄的夜的星空,我推开锈损的门窗,望向窗外四角的星空,渴望在内心与世俗之间,在微凉的键盘上敲下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寻访内心遗落的乡愁。
【作者简介】
费城,原名韦联成。壮族。80后。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一期学员。作品见《诗刊》《民族文学》《青年文学》《星星》《诗选刊》等,部分作品入选各类文学年选。著有诗集《往事书》获第五届广西文艺创作“花山”奖。现居广西凤山。
[责任编辑 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