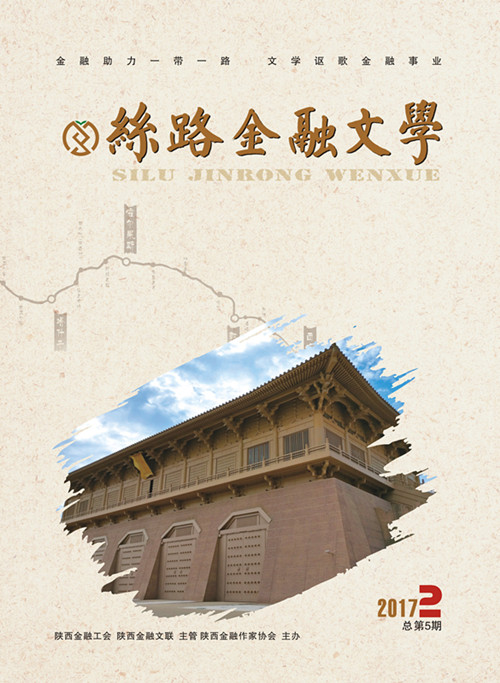扫房除尘后,转眼间就到了腊月二十六。俗话说“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是说在这一天主要筹备过年的肉食。在旧时的关中平原农村,年前杀猪,是杀自家养的猪;割肉,是指没养猪的人家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农耕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生活艰苦,往往在年节时才能吃到肉,故称为“年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位于灞渭三角洲我的家乡西安市郊区新筑人民公社一带(今西安国际港务区)的村堡生产队,在腊月廿六日前后一般都组织人力集中杀猪为社员分年肉。但那时候一切都是统购统销,就是自家养的猪,也必须由供销社统一收购、肉联厂统一宰杀,私自宰杀生猪是要承担政治风险的,即使你杀了猪也不许上市出售,否则就会被定为“投机倒把”罪或者“破坏养猪事业罪”,轻者游街批斗,重则判刑入狱,所以一般人是不敢斗胆撞私自杀猪这条“高压线”的。由于当年供销社出售的大肉一律凭票供应,而农民手里的肉票只有在出售生猪时才给带一两斤,这些大肉根本不够平时塞牙缝,哪里能攒到过年用?因此一到腊月,村人们就眼巴巴地等着生产队杀猪给各家各户分年肉。
我们西王村算是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富裕生产队,有自己的养猪场,除每年向供销社交售一定数量的生猪外,逢年过节总要报经上级批准杀几头猪,让社员群众改善生活、享受一下党的阳光雨露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于是看杀猪成了村人最开心的日子、大快朵颐的前奏曲,也是我儿时最欢悦的时刻之一。
每到杀年猪的日子,不论是冬阳燉燉,还是冬风凛冽,宰杀场上都早早就围满了看杀猪的大人小孩,两张大小相仿、高低相当的小饭桌放在人们围成的不圆不方的圈子中间,只见一名身强力壮的大汉手持长杆铁挠钩(俗称“鋔子”),霎那间钩进一头憨态可掬、不知全然不知大难将至的大肥猪的下颚,奋力向前拉拽,猪儿负痛吱吱哀嚎,大汉毫不心慈手软,另一拉下手的汉子连推带掀,合力将猪挪移到那两张小饭桌前,然后提腿压头,令猪侧卧于小桌上,手持挠钩的壮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戳刀由连嚎带喊的肥猪脖下捅入,直抵心脏,一股带着浓浓腥味的鲜血顿时奔涌而出。不过不必担心猪血会流到地上浪费掉或污染了地面,早有小孩在父母的授意下将搪瓷面盆放在猪脖子下的小饭桌前,时刻准备接猪血回家打牙祭,盆底还放了些许食盐。那时候人人肚子里缺少油水,将鲜猪血带回家在沸水中一煮即凝固成块状,捞出后晾凉,切成小块细条,加上佐料热炒凉拌、蒸煮烩闷都不失为美味佳肴,大人小孩个个垂涎眼馋。也有脸蛋被冬天的寒风冻伤成疮的小孩父母,听说用热猪血涂抹可治冻疮,便挤到前面,以手蘸猪脖下流出的鲜血,直接给自己的孩子左涂右抹,一个个小孩涂抹着非常夸张的红彤彤的脸蛋儿,在人群中挤眉弄眼、相互推搡甚至吐舌做鬼脸,格外抢眼,引逗得人们折腰捧腹。
猪血汩汩地喷了几阵,宰猪大汉意犹未尽,对猪的身体又是一阵挤压揣弄,以期让猪血放尽流净。几分钟前还与同伴们你挤我拱哼哼唧唧叙旧话新的那头大肥猪,此时只有出气而无进气,睁着茫然不解的眼睛,仿佛在问人们我究竟什么时候得罪了你们,见我受难你们竟如此狂欢?我与持刀拿钩的人无怨无仇,他们为何对我刀钩相加?……不论怎么说,随着大肥猪脖子下刀口的鲜血由喷涌到横流以至只冒血泡不再流血,宰猪的壮汉并未立即撒手,唯恐它突然暴起惹起事端,因在别处杀猪时曾遇到过猪带刀狂奔的事情,还发生过猪翻身下桌致使刀伤宰猪人的悲剧,所以宰猪人直到猪毫无反抗的迹象不再呻唤,才敢腾出手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他们中一人用割刀在猪的一只后腿上割出一条五公分左右的切口,再用捅条捅入猪身,在皮下左捅右捅、前捅后捅、上捅下捅,总之让捅条几乎捅遍猪的四肢、双肋和肚皮,然后一人使出浑身力量用嘴对着猪后腿上的切口猪吹气,另一人则用捅条在猪身上有节奏地轻敲慢打,刚开始还显得软瘫的那只猪,经充气后慢慢地变得更加健壮、肥硕了,便用牛皮绳或麻绳扎紧猪后腿的切口。
在离这两张小饭桌不远处,早有一囗大锅下架硬柴火,将锅里的水烧得滚烫,两根山棍横放锅上,宰猪人将那只早已没了生命迹象的猪抬到锅囗的两只山棍上,用水瓢不断地舀锅里的热水朝猪身上浇,那猪纹丝不动,真应了那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话。
经开水一烫,猪毛松软猪皮胀,宰猪剐刀啬石一齐在猪身上大显神威,不一会儿,一头如炭似漆的黑猪便成了如雪似玉的胴体,猪的鬃毛和其它体毛被宰猪人分别置放在锅旁。为了皮肉更加光彩动人,宰猪人还用扫刀将猪身上的脏水不断向外刮,小孩子们高兴地拍手称好。在“给猪洗白白了”、“猪猪明天要去它舅家了”的欢叫声中,猪头被从脖子处齐齐切下,四只蹄脚带腿也被毫不留情的剔除,和绑一起挂在杀猪锅旁边的电线杆上,任人免费观览、品评,由于人多物少,最后只能抓阄决定谁家有口福能享受这些头蹄杂肝。
在杀猪锅的旁边有两棵白杨树,树上横绑一木杠子,两个大铁钩挂在上边。宰猪人将去毛割头的猪倒挂在木杠子上,由后腹向前胸切开,猪的肠子肝花顿时映入眼帘。孩子们不管这些下水如何安顿处置,只关心那只猪尿泡能落到谁手中。在缺少玩具的年代,农村孩子能得到一只猪尿泡吹大揉圆扔耍抛玩当球踢,那也是莫大的幸福和梦寐以求的乐事。大人们则不然,他们有人索要猪苦胆,据说那玩意儿能治手上的疔疮;有人索要猪胰子,据说那东西能治牙痛引出牙根里的某种虫子。我就亲眼见过我村的一中年汉子要了几块猪胰子,用纱布包裹后含在嘴里,只见他蹲在地上、口水直流地等候猪胰子发挥作用。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猪的全身都是宝。”同时也觉得也许猪们不这样想,它们会恨得咬牙切齿地说:“骗子,这全是为了勾引我们这些帅哥靓妹失身而编的谎话!”
这一天高兴的还有那些脚有疼伤(村里人称脚上眨裂眦)的老人,他们认为用泡过猪的热水洗脚可以治脚上的冻疮,便争先恐后地在杀完年猪的大锅里后用盆子舀那稠糊糊油腻腻的烫猪水,然后三五成群的凑在一起泡脚。在甚为惬意地享受泡脚之欢时,他们一边抽着自家地里种植的旱烟,一边谈着当年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决分情况,同时谈论着对来年的生活憧憬甚至是家国大事、亚非拉革命形势,虽说是黄连树下谈琵琶,却也是乐在其中。
我们村那时候分肉不论贫富贵贱,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按人均分,每人一份,即使是地富反坏右家庭的成员也不例外,充分体现了公平化和人性化,因此很多外村的姑娘都以能嫁到我村为婚姻的终极目标和人生的最大荣耀,主要是逢年过节、起码过年能分过一份属于自己的肉吃或孝敬父母。毕竟那时候对于尚未普遍解决温饱问题的普通百姓来说,“炖锅肉吃”绝对是一种奢侈的愿望。不过,过年的时候,这愿望终于可以在我村实现了。那时候,每逢谁家炖大肉,香飘一条街巷、一座甚至几座院子。闻着诱人的香味,缺油水的人们忍不住地流口水,渴望用筷子夹块瘦肉下酒怡情,拣块肥肉夹馍的解馋。一锅炖肉便是人们心中最朴实最丰盛的年夜饭,尽管这锅里肉少菜多,但就是这沾了荤腥的白菜萝卜粉条豆腐,也成了那时候村里父老乡亲朝思暮盼最爱。所以,杀猪割年肉,也成了我少年时代不褪色的记忆。
【作者简介】

白来勤,西安人,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会秘书长,西安市文史馆文史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出版有诗集《圣像与阳光》、散文集《生命礼赞》《墙缝芦苇》及长篇小说《紫金城里哟呵嘿》《雨霖铃》等多部。作品散见于《读者》《散文选刊》《农民文摘》《散文百家》《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文化》及各大晚报。第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获得者,中国金融作家协会首届“德艺双馨”会员称号获得者。
[责任编辑 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