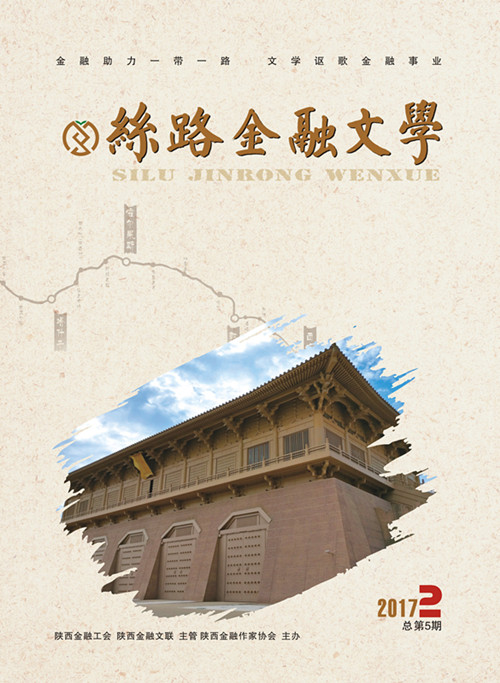三
在夜晚的山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一夜,向军和英子在渺无人烟的秦岭深山迎来了黎明。两人来到不远处一座破庙里,相互依偎着歇下来。
“这么长时间不见来,我还以为红军小哥早忘了英子妹妹呢!”英子嗔怪道。
“哪会呀!”向军连忙解释,“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也一直记着这件事。不过,我记着是记着,但也担心有可能牺牲在长征路上,无法兑现承诺。所以为防不测,我特意写了一封简信装在身上,背面还留下你的地址,希望在我牺牲后,有人将信捎给你,免得你一直牵挂着。”向军说着,就找出一张发黄的纸片递给英子。就见纸片上写着:
亲爱的英子小妹:
哥哥承诺长征胜利后,一定来接你当红军,可是,艰苦卓绝的长征几乎每天都有人倒下。如果我最终没有来接你,请原谅,那我一定是牺牲了。
你的红军小哥向军
“对不起,我错怪你了。”英子看完简信,眼睛湿润了。
“不过,还算幸运,没有过早地去见马克思。你知道,我们那个排当时是32人,后来发展到36人。但最终到延安只剩下11人。逃跑了两个,重伤三个留在地方,其余都牺牲在长征路上。”
“没想到会那么残酷,还真如你说的,随时会有人牺牲。”英子惊恐不已地说,“那个你们叫小老头的柴大哥呢?还有大个子排长呢?他们咋样?”
“排长在多半年后就牺牲了。小老头柴大哥倒没事,大个子牺牲后,接替大个子当了排长。那次在你家给他伤口敷上锅底烟灰还真有效,四五天就好了。后来我也受过两次伤,都是用锅底烟灰敷着消炎治好的。”
“你也受过伤,伤哪了?”听向军这么一说,仿佛伤在自己身上,英子心里狠疼了一下就要察看。
“没事。红军战士受伤那是家常便饭。”向军边笑说,边解开衣服纽扣,就见左肩和右侧前肋各有鸡蛋大一块疤痕。
“大难不死,看来你是有福之人,命大。”英子不无心疼地抚摸着伤口说。
“命是拣回来了”,向军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但是到延安以后,白军一直围困延安,后来抗战爆发,红军全力投入抗日,所以就一直没有条件和机会来。这次是奉命赴西安押运抗战物资,趁着物资尚未备齐,就赶紧来接你。”向军顿一下又说,“不过,毕竟五年没见了,我心里还想着,英子妹妹有可能出嫁了,当不当红军还很难说呢。”
“哪会呀!”英子笑了一下说,“近几年我爹我妈倒是一直在为我找着婆家,可我怎么能答应,我一心想当红军,迟早是要走的人。再说,我心里也早有了一个人,只是不知道人家是咋想的?”
“你心里早有了人了?”向军的心像翻了船似的,一下沉了,急忙扳着英子的双肩使劲摇着问,“你快说,你快说,你心里的人是谁?”
“看把你急的,”英子噗哧一声笑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真的?你心里早就有了我了,那太好了!”向军的脸色一下灿烂起来,“其实我也一样,自那次与你拉钩那一刻起,我就打定主意,不仅要接你出来当红军,还要娶你为妻,而且今生非你不娶!”
“真的?”英子玉润的面庞顿时写满了羞怯和喜色,“那咱拉钩。”
“拉钩就拉钩。”
一只粗壮的手与一只纤柔的手又一次隆重地缠绕在一起:“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之后,向军就势将英子揽进怀里,捧起她娇羞而妩媚的脸庞,忘情地吻着她的丰额、瑶鼻和粉颊,然后将双唇贪婪地停留在她温润的朱唇上。
“英子,咱俩干脆现在就结婚吧?就在这庙里,让观音菩萨作证。”向军拥吻着英子,忽然就有了得寸进尺的想法。
“这也太突然了吧?我还没来得及想这一步呢!”英子嘴里这般说着,心里却巴不得地让自己欣喜地点了头。
然后两人面朝门外跪下来,对天地叩首三拜,又转身对观音菩萨叩首三拜,再转身相互叩首三拜,简陋而庄重的婚礼就这样在暂且成为婚房的破庙里完成了。向军这才挽起英子,却见英子早就一塌糊涂地哭成了泪人儿。
“不哭,今儿是喜事儿。”向军边说边疼爱地为英子拭着泪,拭着拭着,自己也不禁热泪盈眶,旋即,一对新人颤抖不已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水与泪水在紧贴着的两张脸上汇聚成幸福的河流……
休息半日,两人吃了些干粮,继续上路。显然,这是一次艰难却又快乐的长征,已结为夫妻的两人,相互提携着关心着翻山越岭,日夜兼程,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山泉,困了累了就钻进密林歇息,终于第五天午后到达西安古城一个叫七贤庄的普通院落。向军告诉英子,这就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到了“八办”, 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向军和英子立时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大家忙不迭地又是倒茶,又是端来热水让洗脸、洗脚。不一会儿,又端来了热饭热菜。不等天黑,还又给安排好床位,让两人美美地睡了一夜安稳觉。
次日早饭后,向军和英子即肩负物资押运任务,随车队出发,北上延安。
到达延安后,经向军介绍,英子如愿以偿地被编入红军系列,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女战士。不久,又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了一名红军医护人员。
在延安,向军和英子自然与其他众多年轻军人夫妇一样,住窑洞,吃小米饭,穿粗布衣,各自在革命大家庭里过着严肃而紧张的集体生活,没有属于自己的安乐窝,甚至连相聚的时间和机会也很少,只有在某些比较闲松和方便的夜晚,两人相约在一个叫枣耳湾的一丛旱柳下短暂相聚。那段日子,充满艰辛和清苦,但他们感觉过得前所未有的开心和快乐。
然而,这样的日子持续到次年春天即将向夏天交班的时候,情形就开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那天夜晚,在淡淡的月光下,向军和英子披着春夜的温馨,依旧来到早已成为他们固定去处的枣耳湾,在那丛旱柳下相拥着亲热好一会后,向军说:“英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你快说?”
“我请缨去前线抗日被批准了,还有柴进哥,他当我的副手,任副连长,我们一起去。明天就要随又一支八路军部队出发。”
英子知道,此时的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延安很多八路军官兵纷纷请缨去前线抗日,向军也按捺不住对日寇的仇恨而积极请缨。所以,他赴前线抗日似乎已在她的意料之中,但她没想到消息会来得这么快。
“这一去,还不知什么时候能见面。”英子流着眼泪说。
“这个说不准,”向军用手为英子拭着泪,“毛主席说要打持久战,也可能两三年,也可能四五年。反正等赶走了日本鬼子,我会立刻回延安见你。”
“我跟你一起去吧,日本鬼子太可恨了,我也想去前线与你并肩作战。”
“你不去,你去我不放心,你就留在延安吧。”
“不,我就要去,别忘了,人家也是八路军呢。”
“我知道,”向军说,“其实,在后方支前任务也不轻。再说,你已经…..”向军说着就用手轻轻抚摸英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肚子。
算起来,她腹中的小生命已经成长三个多月了。于是她叹息一声说:“那好把,你一定要多加小心,我和他(她)等着你凯旋归来。”
“我保证,抗战胜利之日,就是咱们团聚之时,你我孩子从此永不分离。”向军宣誓般地表态。
“好,那咱拉钩。”英子一如过去与他两次拉钩那样俏皮而认真。
“拉钩就拉钩,你还没忘记老规矩。”向军也如那两次一样,真诚而干脆地响应。一只粗壮的手与一只纤柔的手再次隆重地缠绕在一起:“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两个身影一如既往地靠着旱柳树紧紧相拥,激情缠绵而又难舍难分,直到远山遮挡了月光仍没离去……
四
然后,那个叫枣耳湾的那丛旱柳就孤独了,那些如影随形的欢声笑语从此成为枣耳湾越来越远去的记忆。向军和英子都不会想到,这缠绵的一聚,竟是他们最后一聚,这凄婉的一别,也成了他们生命的永别。
向军奔赴前线半年之后,他和英子爱情的结晶就呱呱坠地了。孩子是个带把的,按照事先两人各取一字取的名字叫向英。从此,英子更加关注抗日前线战况;从此,英子的日子也像前线此起彼伏的硝烟,几乎每天都浓浓地弥漫着望眼欲穿和忐忑不安。可让英子没想到的是,向军走后的岁月,又残酷地复制着当年的情景,他与她一别五年没了任何音讯。直到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之后,也没像他承诺和约定的那样如期归来。
这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欢欣鼓舞的延安军民,潮水般地从各个山沟和窑洞涌出,激情欢呼和庆祝。晚间,到处鼓乐喧天,灯火辉煌,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汇成欢乐的洪流,沸腾于每一山岭河畔。激动不已的英子与医院的姐妹们也早已加入秧歌队,不知疲倦地喧闹和分享着这一历史性的庆典。
次日早上,护士长刘大姐一上班,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的英子便拿着当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日报》,流着热泪对刘大姐说:“大姐,是真的了,日本投降了,我们终于胜利了!”
“傻妹子,谁说不是真的!”刘大姐笑着说。
“昨日闹腾了半天,我感觉像做梦一样,简直不敢相信是事实,今天看了日报,才确信的确是真的。真是太好了,战争终于结束了!”
“你咋不说你那口子终于要回来了?”刘大姐一下说到英子心坎上了,英子撒着娇往刘大姐身上一靠,写满兴奋的脸庞瞬时像彩云般飞起红晕。
但是,英子又兴奋而又度日如年地像手捻佛珠似的捻着每一个日子,整整捻过去了一个月,也没见向军的消息和身影。
正当英子喜悦的神情逐渐被焦虑摧残贻尽,愁绪像阴云重又悄然笼罩了灿烂的面庞时,延安红军医院收治了一名从华北抗日前线转来的八路军伤员。他的头部面部严重受伤,整个脑袋被横七竖八的绷带紧紧包裹着,只有眼睛和嘴巴各留一条缝。本来他已被安排在当地医院救治,但他心里有事,坚持要回延安一趟。
尽管从面部无法看出这名伤员是谁,但英子还是从他清瘦的身体特征和瓮声瓮气的说话声音中认出是柴进。
“哎,这不是我柴大哥吗?”英子异常惊喜地问。
“我是。”他说,“你是英子?”
“我是。”她说,“你们到底回来了。”
英子下意识地把“你”说成集合词“你们”。随行的战友回来了,那么向军就也该出现了。因此接下来,自然是英子抑住狂跳的心,等待着柴哥告诉关于向军的消息。但是等了好一会,柴哥没说。仿佛向军与他根本无关。
“柴大哥,你回来了,他呢?”英子终于迫不及待地问。
“他……”柴进迟疑了一下,却说:“英子,你也是军人,希望你像向营长一样坚强。”
柴哥不肯明说,英子还是听出了画外音。她万万没想到,长途跋涉地苦苦思念和盼望了五年,盼来的竟是这么一句话,头就“嗡”地一声,眼前一黑,身子像面条一样软了下去。医护人员立即将英子抬至另一张病床上,手忙脚乱地施救,好半天英子才又醒了过来。
“柴大哥你倒是说啊,他到底怎么回事?”英子稍稍静了静,就又问起柴进。
“让他自己说吧,这是他给你的信。”柴进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用草纸包着的小包递给英子。
英子极其郑重地接过小包,像接过一件珍宝,轻轻打开一层层草纸,露出两枚分别由华北战区八路军颁发的一等奖章和晋察冀军区颁发的特功奖章,以及一方折叠齐整的手帕和同样折了几折的一页信纸。手帕是那年向军离开上村时她送给他的,没想到十年后又几乎全新地回到她手里。她将奖章和手帕捧至面庞深情地吻一遍,又深情地吻一遍,这才打开那页发黄的信纸。
亲爱的英子:
我答应你,等抗战胜利了,马上回来团聚,你我都殷切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但是,如果到了我该回来的那一天,我仍没回来,那就一定是牺牲了,回不来了。那样的话,请你不要为我难过,你也是军人,你知道作为一名军人的使命。
遗憾的是,我没能够见到我们的孩子向英(我想他一定是男孩,因为你怀他的时候爱吃酸),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请你抚养好他,长大了,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为打击侵略者而死,是为保卫祖国而死,他应该感到自豪和骄傲。
你的向军小哥 1940年4月28日
读完信,沉痛的英子默哀了好一会,又突然发现了疑点,便说:“不对,柴大哥,这是几年前写的,怎能说明他……”
“没错,是几年前写的”,柴进说,“上前线以后,向军就写了遗书交给我,说如果他牺牲了,让我替他转交给你。”
英子这才点一下头,自言自语道:“他是随时准备牺牲的,这已经是他给我的第二封遗书了。他是说过,红军战士自参军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革命了。”
英子悲伤地叹一口气,竭力把自己镇静下来,颤抖着声音说:“向军,咱俩拉了三次钩,你对我有三次承诺,前两次兑现了,这一次你食言了。说好‘抗战胜利之日,就是咱们团聚之时,你我孩子从此永不分离’,你怎么就忘了呢?”
“他没有忘”,柴进说,“他一直牵挂着你,盼着早日与你团聚。我军实施战略反攻以后,已升为营长的他更是心情不错地对我说,估计日寇嚣张不了多久了,我们终于要和家人团聚了。等抗战一结束,我就立即回延安见我媳妇见我孩子。”
“但是,战争是无情的”,柴进接着说,“活过了今天,未必能活过明天。向营长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夜牺牲的。就在日本投降的前十几天,向营长率领军民连续端掉了日军设在战略要地的四座炮楼,歼灭守敌一百余人。次日,日军调集重兵突然向我营阵地发动报复性进攻,数倍于我的敌军很快对我军民形成了包围。情急之下,向营长命令我率全营战士迅速组织群众撤退,自己则率一个班作正面阻击掩护。眼见敌人像蝗虫一样黑压压地扑上来,向营长和全班战士就要被活捉,他端起机枪,如雄狮猛虎般跳出战壕,猛烈扫射,敌人倒下了一片又一片,嚣张气焰再次被压制,军民冲出重围,得以安全撤离。而他和全班战士终因寡不敌众和弹药不济而壮烈牺牲。”
听了柴哥的讲述,英子极其疼楚地叹惜一声:“可惜他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然后闭着眼睛靠着床头沉默好一会。之后,缓缓睁开眼睛,又一次捧起遗书,一字一句地读一遍着,拼命压抑的悲伤,使纤弱的双肩不由地剧烈颤抖起来,汪在眼里的泪水,如山泉一滴又一滴地溅落在遗书上。
然后,每日在红军医院没黑没夜地护理伤病员的英子,就也成了病员。而且病得不轻,一连几天粒米不进。
柴进得知后,内心不由地涌起莫大的酸楚和不安。这日早上,他不顾护士的阻拦,一步步挪着虚弱的身子,来到英子那孔窑洞病房。就见原本比较丰腴的英子一下瘦了一大圈,玉润鲜亮的脸色变得灰暗而惨白,美丽的双眼也失去了往日的水灵和妩媚而变得呆滞和失神,以致有人进来她都全然不知。
“这才几天,人就成了这样!”柴进不无心酸地自言自语。
英子闻声,这才发觉柴哥立在床前,急忙让在凳子上坐下,然后由护士搀扶着坐起来,靠在床头,吃力地说:“柴大哥,你伤还没好,不敢乱动的。”
“我没事。”柴进说,“英子,你不能这样,你要这样,向军不能安息,我也就无法安心养伤了。你柴大哥嘴笨,不会劝人,我要说的还是那句话,你也是军人,你该像向营长一样坚强才是。”
“嗯嗯。”英子紧咬住嘴唇直点着头,眼泪却又无声地流着、流着,纤弱的双肩又一次剧烈地颤抖起来。
一直在身边照顾着英子的刘大姐不无心疼地搂住英子的肩膀说:“好妹子,你就哭吧,想哭就哭出来,不敢这么憋着。咱男人走了,咋能不哭。”英子一头埋进大姐胸怀,哇地哭出声来,压抑在心中的巨大悲伤,像开了闸的水库倾涌而下,极其悲恸的哭声,冲出窑洞病房,撕扯着整个医院的空气,令在场的柴进和医护人员无不凄然泪下。
任由英子悲天跄地痛哭了好一会之后,刘大姐这才边为英子拭着泪边说:“好了妹子,咱不哭了,柴哥说的对,咱也是军人,咱还有使命,咱还有孩子。你知道,我男人上抗日前线第二年就战死疆场,和你男人一样,都是铁汉子,都是抗日英雄,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坚强不屈……”
刘大姐这么一劝说,英子渐渐止住哭,情绪总算平静下来。她长长地叹息一声,哽咽着对柴进说:“柴大哥,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知道。在太行山下。当地乡亲将他和其它同时牺牲的战士安埋在村头的一片小树林里,立了一块简易石碑。”
英子沉默许久,复又拿起遗物,沉吟地说:“向军,每一次的关键时刻,你总对我有个承诺,我想我现在也该给你一个承诺了——你的英子决不弃你于异域他乡,我一定会很快去看你,然后接你回我老家上村,你喜欢上村红石岩那地儿,就让红石岩成为你的归宿吧。”
然后英子对柴进说:“柴大哥,你好好养伤,养好了伤,你带我去看他,接他回我老家,我们从此再不分离,免得他孤独和牵挂。”
“这样最好。”柴进慰籍地点着头,“那我也给你一个承诺吧,我一定带你去,一定帮你了却这桩心愿。”在场的刘大姐和医护人员无不敬佩而赞赏地点着头。
一月之后,柴进完全康复。康复的柴进当然没有忘记他对英子的承诺。于是这日早上刚上班,趁着英子来查房时,柴进说:“英子,我们出发吧?”
“嗯,出发!”英子重重地点着头说。她显然也在期待着他说这句话。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柴进接到医院转交的一纸电报:团长任命他接替向军任营长,并命令立即归队,参加对国军作战。
出乎意料的变故,一下打乱了柴进与英子的计划。柴进歉意地握着英子的手说:“英子,对不起,国共内战打响了,我马上要归队,无法带你去看他,而且那里又将是战场,你也无法接走他。”
“又要打仗了!”英子不无遗憾地叹一口气说,“去吧。我也是军人,我懂。”
“请相信我,等战争结束后,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来接你去。你和孩子多多保重。”
“谢谢,你也多保重,我等你。”英子由衷地叮咛着,轻柔的声音明显地哽咽起来,身子不由地向他怀里轻轻一靠。
“我等你!”简简单单的三个字,蕴含着怎样的分量和信息,柴进一时难以品味出来,但他深深理解,这对行将奔赴战场的他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温暖和力量,也更意味着无牵无挂的他从此就有了一份牵挂。他心里不禁一热,就势将她紧紧一搂……
三年之后,也就是解放战争胜利之后的次年春天,胸前佩戴着人民英雄奖章的柴进终于如约出现在殷切期盼的英子面前。
然后时过不久,上村白石岩下的苍松翠柏间,一座坟丘湿漉漉地拢起来,一尊硕大的黑色石碑随之立在坟前。碑上庄重而醒目地镌刻着一行白色大字:
抗日烈士向军及爱妻英子之墓
[责任编辑:云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