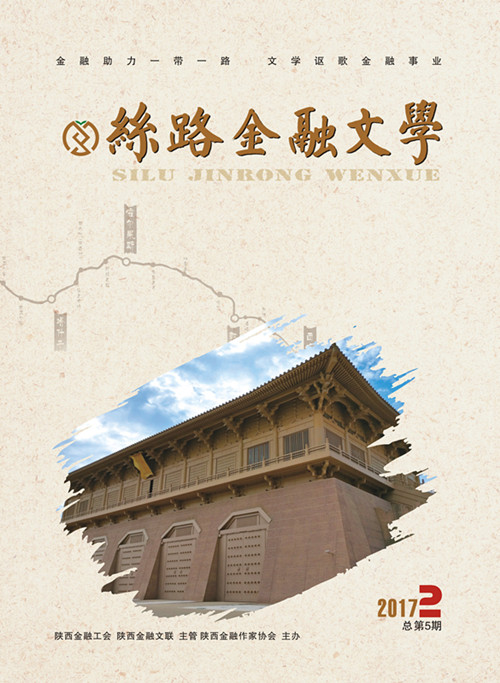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一)
假如我是一个长相平平最多只能用不丑来形容的女孩,请别叫我美女,谢谢。
指尖在键盘上吹鼾
时而急促时而迟疑
时而让人痛苦而煎熬
等待另一只靴子落地
昨晚的门缝夹过的脑袋
半道血痕爬进发际
周围的人成了移动的树
脚下的路早已小儿麻痹
.
类似磕药过量的目光
散发出荷尔蒙的腥味
与女神意念中全裸相拥
跨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
一片绿茵发春似的疯长
睡梦中太阳突然就阳痿
飘逸轻薄的一袭绿罗衫
衫中跌宕的贪欲如痴如醉
母狗与公鱼一度交配
玫瑰娇羞地与马桶嫁接
.
一只脚在粪坑中挣扎
另一只脚踏在山冈
山冈上正风景旖旎
月光从西瓜上滑倒时
十分痛楚地呜咽抽泣
雪白花红叶绿的废话
需一遍又一遍地叨絮
以便让世界上所有的脑
要么瘫痪要么残疾
码字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就像低头族刷微信抢红包;创作是一种表达,就像出汗放屁打喷嚏和被咯吱后忍不住发笑等等。有些事注定要发生,就让它发生吧,但千万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金融人玩金钱,文学人玩意境,雅俗之间,如上市公司跨界重组。
(二)
电影《绝世瑶妃》主创人员聚会,文人骚客美酒佳肴,这样的场合自然少不了美女。女一号盘凤飞的扮演者吴恙是个湘妹子,美人姗姗来迟,惊艳登场,酒桌上的男人们顿时雀跃起来;各具神态,争相表现,不在话下。正是应了“酒色才气”几个字。
如今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结集出版者众,拿三两万元钱出版社就给你出了,只要不触碰底线,如不能有性过程和性享受描写等等。其实,纸质图书发行个五千册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微信QQ朋友圈里广泛传播,多是看也没看就点个赞、捧个场;签名送书,恭请雅正指教惠存;开个作品研讨会,一片赞扬,主题突出结构奇妙人物鲜活语言流畅,当然,但是……提一条不成熟的意见或者建议收场,不痛不痒,再也不会有下文。电影不一样,人家千万上亿投入,图的是产出效益和票房。所有的剧本讨论会都是万箭齐发,刺痛自尊心的批判,体无完肤,颠覆你自以为是自鸣得意的构思。
老婆是人家的漂亮,作品是自己的高明。
文人都是一种怪物,自尊心自信心都特别强。
某电影编剧是一个国内非常著名的作家,写小说的,作品畅销。在剧本讨论会上,眼见著名作家被批得脸红脖子粗,无地自容,恼羞成怒,最后扬长而去,临走抛下一句话:“你们不懂!”从此再也不见这位知名作家染指电影。
我想起了一句近来流传甚广的名言:很多人关心你飞得多远,却鲜有人关心你飞得多累。盛名之下,背后异常艰辛。二爷的几部电影剧本先后十数次易稿,我读了其中至少三四稿,提了很多意见;十条意见有一条被采纳都是我的荣幸。
“没有一只麻雀掉下来上帝不知道。”一个作家也应该知道掉进他的世界中的每一只麻雀(罗伯特·麦基《故事》)。
高兴的事当然可以在朋友面前一起分享;不求有难同当,但求有福同享。分担内心的郁闷、步履的艰难,则只能在兄弟之间;开怀畅饮,似醉非醉,酒桌上其他人走尽之后,可以放开心思,毫无顾忌地相互倾诉内心的痛楚。
正是腊月,快过年了。
年怎么过?
多年的哥们中午喝了些酒,坐在我办公桌的对面,说着说着就忍不住落泪。老娘突然就中了风,加上老年疵呆,请的保姆换了七八轮,一个个都被老娘骂走了;马上年关了,新来的保姆要回家过年,这个年怕是有的忙,兄弟们估计分不出时间一起小聚畅饮。
沉重的负担,压弯了男人的背脊,男人天生就是一道承重墙。
尤其是这样的年龄,父母高龄,说走就会走,看一眼是一眼;为儿女一辈的家庭事业前途,得拿出毕生的积蓄,用年过半百的身躯和心血打拼,只想为他们更多地付出;期待孙辈的到来,把早已榨干的身躯做他们的玩伴。
上天总有走眼的时候,折腾我年轻善良的兄弟……
开心的事可以多说,不顺心的事就不再说了,说了也没有意义。
到了这样的年龄,一些事肯定要发生。
(三)
乡下的空气真好!
尤其让人羡慕的是堂屋门前,长长晒衣杆挑着被褥衣物在冬日的暖阳下曝晒的场景,满身白毛的狗在水泥地坪上懒洋洋地瞌睡,屋前屋后的高树在正午的阳光下投出短短的阴影。
刚刚吃完小年饭,妻陪着老娘在厨房里收拾碗筷。老父亲从厨房的土灶上的横梁上取下一块一块熏熟了腊肉,装进一只硕大的编织袋,叫孙女喊我打开车的后备箱。
这时,我正在查看放在后屋里的两副棺木,黑色透亮的油漆,被父亲不时地擦拭保养;大概二十年前就做好了,每一年都要加一层油漆,父亲亲自监工。屋侧山嘴上的墓也早在七八年前落成,两座拱型的墓穴,墓前麻石墓碑镌刻了他们的名字,孝子贤孙列后,墓志铭请了当年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撰写的。
朋友讲的一个段子:一哥们去了趟香港,前后一个月时间。回来已是傍晚,夕阳照着他的脸,江风吹拂他额前的短发和披在身上的风衣的下摆;江的两岸,鳞次栉比的楼房林立。他一只脚踏在大桥的石墩上,向远处眺望,一时感慨万千:家乡的变化真大啊!
腊月,快过年了,我从北京回来。
在北京一呆大半年,回家总有这样那样不适应,鼻子有点堵塞,拉了一回肚子,妻的脸色有些严肃:是不是水土不服啊?
弟兄们陆续见了面,本来并不纯正的口音让舌头更加无所适从。
女儿突然对我说:老爸这些年为什么话也少多了,没有了以前的风趣幽默,心情不好或者有什么心事?没有的事,闺女,大概老爸是老了;没有不开心,更没有什么心事,只是不再喜形于色怒形于色罢。因为我知道了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终会走,该发生的肯定会发生。
万事顺其自然。
在女儿眼里,乡下七十多快八十的爷爷奶奶和城里八十有几快九十的外公外婆才是真的老了。
丁酉腊月/零碎记忆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