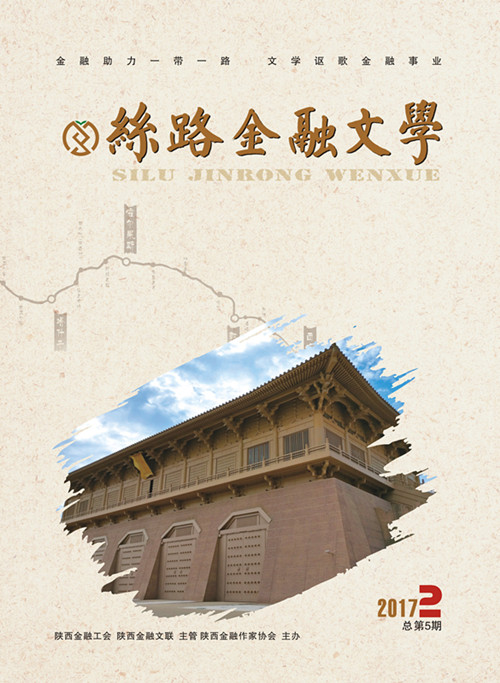这样的好运持续了好几次,麻子异常兴奋,为避嫌,小心将剥好的野兽皮晾干,悄悄送到别的地方,甚至是邻县的供销社买,剥下的肉用大缸腌制起来。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麻子打猎的事被眼尖人发现,消息很快就传出了,公社武装部长带人持枪连夜将他的门踹开。
这个六亲不认的转业军人让长岗人提起不寒而栗——肃反那年,他带人将躲到山里、曾经当过伪保长的父亲抓到,捆住交与县公安,公判大会后,他手持步枪击毙了自己的亲生老子!他立场坚定,神采奕奕,戴着大红花红遍了全县......这个矮胖部长曾在多次批斗会上拳击麻子,不知为啥,他不打别人,专打麻子,是骨子里对俘虏的一种仇恨吧!有一次将麻子头按在地上,磕掉了一颗牙齿,麻子满口的血狠狠地吐在他的脸上......眼下幽暗的屋里透着腥臊味,壁上挂着刚剥不久,用苗竹撑开的兔皮,黄鼠狼皮,盆里尚有一些流着血的野兔,野鸡,斑竹鸟,枪与火药在柴堆里找到了,麻子被五花大绑押到了公社。
面前的办公桌摆着纸笔,要求写出私藏枪支的经过与动机,麻子一宿未睡,被人松了绑。快到午饭时间,从里间屋里起床的部长打着哈欠,无精打采地泡了一杯茶,拉张椅子坐到了他对面,看到歪歪斜斜的几个字,很不满意,他用粗壮的手指敲着着子:
你要老实交代,你私藏枪支不仅仅是打猎,是想趁机报复杀人还是拦路抢劫?
瞎说,我仅仅是打猎,搞点野兽皮,换点油盐钱!
你的问题复杂,新来的区革委会主任对你在朝鲜战场通敌投降一事很重视,你顺便把经过也写出来吧。
狗屁,狗屁呀!麻子似乎被激怒了,不停地用双手左右扇自己的耳光,嘴角流出了殷红的血。
哼,装疯卖傻,不老实,那我只好把你交区里了,到那里可没有你好日子过。何处何从,你自己选择。想到麻子那次当人面不服管教,将嘴里磕出血吐到自己脸上丢了面子,部长不耐烦的“咚咚”抡拳捶着桌子。
麻子耸拉着脑袋,在无力的摇头。
妈的,来人,把徐来狗来绑了!部长提起精神,来到麻子身后,猛地抓住了他的后衣领倒拖着,大声吆喝着,麻子连人带凳差点翻到。
又要挨捆,挨打,挨折磨,这样生不如死的日子不止一次在脑海里出现。麻子已经饥肠辘辘,昏昏沉沉,不知哪来的力气挣脱弹跳了起来,没容绳索套上脖子,对着上来的人“砰砰”就是两拳,顺势抬脚将来人踢到。麻子手脚麻利,枪法准,再加上面相丑陋凶恶,适宜于做保镖,在国军被挑选任师团长警卫,学过擒拿格斗术。
来人哪,来人哪!部长破嗓子狂叫着,迅速冲向里屋,准备到柜里取枪,被失去理智的麻子一下子扑倒在地,双手铁钳一样掐住了脖子,“嗷嗷”叫着。
老子活腻了,活够了,狗鸡巴日的,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我们一块死吧......麻子怒吼着,脸如猪血般红涨,用膝盖压住部长胸脯,改左手掐住他的脖子,抽出右拳雨点般砸在他的头上,脸上,部长皮开肉绽,命悬一线,及时赶来的人乱棍打昏了他,救了部长一命。
围观的人墙里,麻子醒了,口里仅有一丝气息,像个怪物一样,破大衣裹着身子,头发蓬乱,被民警翻过身子,拷上双手,脚上镣,抬起来摔进后备箱。警车尖叫着分开人群,车轮杨着尘土远去。
麻子打伤了公社武装部长,被刑事收监,不多久,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发配到四面环水的宿松九城畈农场劳改。
又是几年过去了,麻子已是四十开外,这时他仍是单身,虽长年在生产队出满勤,也只能是按工分值分点口粮,糊饱肚子,好在他有力气,帮人家做屋印砖,挑砖,到山里驮树,吃六大盘,解馋。他的食量惊人,那年秋天我家做屋印砖,麻子母舅从田里挑着百余斤的砖泥,踩滑了,滚到了田里,像个泥人,引起一阵哄笑,爬起来,脚崴了,仍在咬牙坚持挑着。晚上餐桌两瓦钵红烧肉,他吃了一钵,外加约一斤饭,一瓶酒才打着嗝饱,桌上人都看着笑了,据说他吃一顿能管一天,做事累了,能睡几天几夜,家里门敲破了不应,像死人一样。
母舅也想找个伴,没人愿嫁他,就连岗后死了男人的跛子寡妇也不愿沾他的边,媒人带他提着猪肉挂面上门,她躲避瘟疫一样锁门走了,她说麻子饭量太大了,吃穷了。人到中年,他头发花白,酗酒如命,脸色如猪肝一样,瘦高的身板有些弯曲,仍显得硬朗,犀利的眼神,显示出他的野性犹在,在封山育林年代,麻子被大队选中做护林员,年补一个劳动力的工分值。
光阴迅速,转眼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全国上下的拨乱反正,岗前岗后的地主富农陆续在摘帽,下放的右派伸直了腰,陆续返城工作。然而对于徐来狗的“坏份子”摘帽却遇上了阻力,县革委会落实政策办公室对全县唯一的抗美援朝俘虏兵不能下结论,没有找到可比性文件,在等待上面答复。
麻子仍在大队做护林员,与以往在生产队上工不一样,时间自由支配,连日来不停的在大队,公社转,他让当民办教师的侄子为自己写申诉材料。
冬夜来临了,在家里简陋的瓦屋堂厅,麻子烧了一盆栗碳火,北风透过破裂的木窗玻璃钻进来,刮得碳火“丝丝”响,火苗乱窜。他炒了一瓢香喷喷的沙地花生放在侄子面前,不停地说,侄子记录加工,一段一段读与他听,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东西说过后在不断补充,调整,他剥着花生壳,吹去掌心中的红薄花生皮,将香脆的仁放在碗里,又从碗里倒侄子手心里,催侄子吃,零散的有多天的夜晚。十余天过去了,麻子接过写好的十几页材料揣进怀里,又按按,感觉自己摘帽的时间不会太久,也许就在年前,或许在来年春天的某个日子,心里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
1979年底,十八里长岗拨乱反正仅剩抗美援朝俘虏兵徐来狗未落实,其余摘帽基本完成。尽管仍然沿袭大集体农耕模式,但包产到户的风声已经传出,人们在等待着,期盼着责任田到户能吃饱穿暖,能带来生的希望。
这时的长岗是平静的,没有了运动来临时那激情澎湃的群众批斗会,没有了老贫农忆苦思甜的声泪俱下,没有了学大寨造梯田、捏紧裤带树典型的狂热......
进入腊月天寒地冻,小麦,油菜下种后,就到了农闲季节。此时长岗人大多龟缩在家,减少体能消耗,一天只吃两餐,可节省点粮食抵御来年春荒。一个晴暖的上午,弟妹一帮人来了。这是三间小瓦屋的家,屋顶矮的似乎就在头上,外间土砖搭的锅台连坐场。中间的房光线昏暗,结满了蜘蛛网,床上的麻子已有一星期上吐下泻,吃了旺狗找赤脚医生开的中药才有所好转。这不,他支撑着起来,搬了凳出来晒太阳,招呼着弟妹坐在身边,从袄子里层掏出皱巴巴的香烟递与旺狗,掏出火机帮他燃上,自己吸着,猛烈地咳着,好一阵才缓过来。
哥,那事我也找大队公社了,说材料报到县里,还没消息。等吧,不批也就算了,你都老了,也无所谓了。旺狗坐在长凳的一头,吸着烟,一脸的无奈。哥哥是长岗,也许是全县唯一没有摘帽的,这也是他们愤愤不平的。
哥,不自找苦吃了,你老了,有我们吃的就有你的,不要想那些了吧。背有些驼的大妹说着取下肩上的包放下,里面装了一些鸡蛋,腊肉,挂面,听说哥病重,她是从山里搭车赶来的。
对于哥哥,徐家弟妹有一种归属感。长岗俗话说,父母离世,长哥当父,长嫂当母。也有说,家因此就散了。这个丑陋粗暴的兄长毕竟与终日同泥土为伴的庄稼人有着不一般的经历,不一般的见解,与兄妹抱团共同经历着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隔壁的旺狗患腰脊椎劳损,多年不能挑驮,家有事,他总是主动帮忙,几次做屋都帮印砖,挑砖,抬石头,此外帮平整菜园地,上山打柴火等。对待几个妹妹更是情有独钟,两个嫁到山里的妹妹遇到不顺气的事,总是回来向娘家大哥倾诉,遇这事麻子不护她们,说夫妻争吵是免不掉的,不护,催她们回家,但对大妹婿与邻村寡妇有染一事却发怒了——他气冲冲赶到了山里,躲在屋角的瘦猴妹婿被他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拖到了里屋,他抡起了铁拳,然而只是在半空,没下来,在长岗有句谚语——除了郎舅无好亲哪......那时打猎总是把腌制的兔,黄鼠狼后腿悄悄送去,偶尔留住几天,也不闲着,帮田里,地里干着活,他有的是力气。而妹妹也是倾其所有,将家里的腌腊肉,鸡蛋煮上大碗拌挂面,有时也杀一只下蛋的鸡来招待哥哥,每当这时,吃肉,喝着酒的麻子总感到一种无比的幸福,似乎自己成了人间最快乐的人!那次小外甥抽筋高烧不退,他想起獐子睾丸烤干碾碎服下能管用,跑到了对面怀宁的一猎户家,讨到了用火烤干,碾碎包好,连夜送到五十里以外的山里小妹家……
前些天,麻子带着材料仍然在找大队,公社,要求恢复军籍,取消“坏份子”帽子,他穿着一件黄大衣,扣子掉了,用麻老布腰带捆着腰,高高的个子明显弯曲了,蓬乱的花白头发,脸如刀削,由黑转黄,麻点呈土灰色,如同逃荒的一般。遇开会,他就坐在走廊上等,整整一上午或者一天,也没看见他吃啥、喝啥,总是低着头在抽烟,眼前一大圈烟蒂,是一阵接一阵剧烈咳嗽引起了过往人的关注,这个可怜的抗美援朝老兵,上面没有政策,我们也无能为力呀!见到的人叹息着:老徐你回家吧,有消息就通知你,不用跑路了。
太阳升高了,无风,长岗上暖融融的,老屋的一角,小妹在他家灶台做了一大锅南瓜饭,焖了一瓦罐黄豆,沾了一点香油,炒了一大碗腌辣椒伴蒜头。日到头顶,一家人回到屋里,围坐在一起吃的津津有味,体质虚弱的麻子吃了一点靠在椅子上,往常他喜欢吃的腌辣椒,今天却没沾。饭后,他抽着烟,指着门边已装好的几袋红薯,说你们顺便带回家,我要到县里去伸冤,为的是不为自己死后留骂名,不为家族背黑锅,不达目的不罢休。
三天后的夜里,从县里回来的麻子发出凄厉的哭声,声音一会低沉,一会狂吼,像狼嚎,像中枪猎物的嘶叫,令人毛骨悚然,惊动了左邻右舍!长岗人从未听过这种哭,大家三三两两来到麻子的小屋,围坐在他的床沿,旺狗说老大到了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说要等上面文件,问要等多久?对方说搞不清,问的有些厌烦了,说谁叫你怕死当俘虏呢?谁叫你背叛祖国呢?像你这种情况也许没有平反政策吧,我们认为也不能为你这种人平反!答复就有些伤人了。临近下班时间,哥哥被工作人员从凳上拎起,几乎是推搡出了办公室,病后的他已无半点挣扎之力,差点从台阶上栽下来。
夜深了,左邻右舍在叹息中离开了麻子。
县城之行让麻子绝望了!同时感到难受的右下腹从隐痛到加重,怕油,呕吐,发烧,脸色蜡黄,旺狗陪他去了公社卫生院,检查说是酗酒引起肝病变,要去县医院诊断,从医生与老二悄悄耳语中,麻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续多日,他用手按,用椅子靠背顶住肝区,痛的大汗淋漓,冥冥中感到大限到了,活在世上是个累赘!
腊月二十八的早上,长岗东边的歪脖松树干上,早起的人发现有人用一根粗壮的麻绳上吊了,舌头伸出一大截,脚下是踹翻的凳子,这一年,麻子年满50岁。
岗前岗后的人都来了,山里的妹妹,妹婿急匆匆赶来了,躺在大门板上的哥哥骨瘦如柴,颈脖被绳子勒出了深痕,血迹犹在,脸被几叠黄表纸盖着,一家人抱头抱脚痛哭流涕......
麻子尸体被乡村老人用雪白的棉纱从头到脚裹着收殓,装在棺木里,覆盖石灰,木炭,然后合上盖子,用大钉钉牢四角,半夜由四个青壮劳力用竹杠系着麻绳,吆喝着抬出去的,我父母去了,买了鞭纸为他送老归山,我妈哭的很厉害,头七,满七都去了,我是后来得知的。
麻子死后七个月,县里穿军装的人送来了摘帽通知书,内容如下:
根据中共中央1980{74}号文件《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复查处理意见》规定,经县落实政策小组调查核实,报经批准,决定对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第9兵团27军226排机枪班被俘战士徐来狗恢复军籍,享受同等复退军人待遇,撤销原昌图志愿军规管办所做的“叛国投降”等错误决定,同时取消当地政府所划定的“坏份子”称号......
周边男女老少从田里,地里相继聚到旺狗家的屋场,听到了军人宣读的这一不同寻常的、心酸的决定!
次日,一个燥热的午后,旺狗带着一家人来到哥哥的厝基地,教书的侄子读着摘帽的决定,哽咽着。
长岗的丛树林地带,成梯形,一处又一处的新老厝基横七竖八。这里殡葬沿袭了几百年的习俗,人死后不会直接下葬,而是先安放在野外,三年后开棺取出人的骸骨擦干净下葬,称之为厝基。相传是安庆地区的先人来自江西瓦屑坝,后因为讨生活来到此地,原本指望人死后可以暂放遗体,以后可以带到故乡安葬,后来定居下来,渐渐形成的风俗。
麻子的厝基上用铁丝绑棺底,棺上捆着厚厚的稻草,两头用大青砖垫底,用砖砌成网状,两边躶露红漆棺木。麻子无家无后,老二旺狗承担了他的后事,眼下,他接过儿子手中盖着红印章的公文,拿出火机点燃了。哥,把平反决定烧与你,你就安心了。你在世待我们好,我家保留了你的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记得你!三年后,把你葬老坟山,与父母一起啊!
呜......旺狗哭了,风吹来了,松涛阵阵,头顶上骄阳似火,树林里,蝉声断断续续,有气无力,没有入夏时的高亢激昂,池塘的涵洞在放水,浇灌下面的庄稼,大多只有半塘水,塘边有青蛙的合唱,鱼搁浅跳跃、追逐、不时泛起阵阵浑水。山坡上,野草被烈日烤的泛黄,还有不知名的野花卷缩着,都在期待一场着雨水的来临。三伏天到了,人忙,牛喘……农家最忙的“双抢”季节。
日子好快,一晃,是三十年以后了!去年秋后的一天,我来到长岗,眼前秋天的田地一片萧瑟,乡村青壮劳力大多外出打工。如今的农事除了麦收,就是每年一季的稻子了,虽然也有零星的晚稻闪着金黄,极不协调地点缀着大片的抛荒田地,难以掩饰其荒凉、沧桑。是的,今非昔比,一切都得顺应天时!长岗乡村午饭,接近下午一点,这点与童年的记忆一样,乡村劳作的时间长,午饭是太阳过顶后。鬓发有些斑白,当教师已经退休了的老表与我滔滔不绝说着他的大伯,宽敞的餐厅里,坐的是上了岁数的乡亲乡邻,满满的一桌好菜,我们边饮边聊......如今,老表在老屋基上盖起了几百平米的别墅房,新修的村村通水泥路四通八达,这里做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面貌焕然一新。麻子老二,我称二母舅的旺狗也已西去多年,一切都将过去,然而,我却在老表家见到了那枚暗红色的抗美援朝纪念章!这章为铜质,外形为五角星状,上方书“和平万岁”,中间主图是一只和平鸽,四周是红色烤漆,章的外环与和平鸽表面均镀金。章背铸有“抗美援朝纪念,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1953年10月25日”的文字。尽管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章依旧如新!
席间,老表说起了美国大片《血战长津湖》,那是一场令美国人肃然起敬的鏖战啊!美军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师和第3、第7步兵师,以及韩国第1军团联军,约10万人,与志愿军第9兵团,由20军,26军和27军组成的近15万人,在零下30-40度的严寒中血战20天之后告负!美军残部在7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利用海路逃离战场,这也意味着“联合国军”全部被逐出朝鲜东北部。
已经有些醉意的老表竟然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了,“雄赳赳,气昂昂,跨国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歌声雄壮粗犷,有十八里长岗汉子的野性。都喝高了,我的思绪随着歌声飘过鸭绿江,三八线,上甘岭,金城,长津湖,板门店......我的穿着草绿色军服,帽带红五星的前辈----百万英勇的抗美援朝将士,将骄横不可一世、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彻底击溃,如同美国陆军上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美军司令官”。历史鉴证与记载了这灿烂辉煌的一刻,我百万志愿军抗击美韩联军的英勇壮举,感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穿越五十年的时空,数以十万计的铁血男儿魂断异乡!那些活着回来的,大多靠自食其力养家糊口,艰难度日,还有散落在城乡角落的战俘像猪狗一样没有尊严地活着,身心煎熬,他们当中很多人英年早逝,熬不到平反的那刻,健在的应都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已经是寥寥无几!
黄昏时分,我与老表来到不远处的徐家祖坟,那边角竖碑埋葬的是徐来狗的尸骨——我老家的亲房母舅,一位可敬可悲的抗美援朝老兵!一长约十余米垒起的不规则坟包,荒草萋萋,枯枝缠绕,排列着长短不一的石碑,有些碑的字迹已经模糊,无法辨认。边角黑色墓碑有些破损,大半截已埋进土里,但上侧面“徐来狗老大人之墓”字样仍清晰可见。我买了花炮鞭纸,在燃放。我与老表跪在他的墓碑前,磕头,磕头,再磕头! 此时我想,人生好多东西是命中注定的,我的麻子母舅该战死在朝鲜,或在集中营里被美国人扔进海里喂鱼,一死了之免遭活受罪。那个土耳其兵为啥救他?是人性的本能,还是对战争创伤的一种同病相怜?救他,其实也害了他,还有那颗不响的臭弹!如果不俘虏,做为机枪班的壮士凯旋回来会是怎样的一种荣归故里?怎样的一路鲜花?俘虏后,如果被国军策反去了台湾又会是怎样一种结果?也许,也许......也许已病死于台北,台中,台南或台湾的其它地方,也许还健在,那又会怎样呢?
作者简介:
操柏森,男,1963年生,毕业南京农业大学,现供职安徽潜山县农业银行。安庆潜山作协会员。曾在《中国旅游报》、《中国矿业报》、《安徽日报》、《安庆晚报》、《中国工人》、《金融文坛》、《庐江文学》、《安徽佛教》、《安徽农村金融》、《金融作协》、《陕西金融作协》、《天柱山文艺》、《天柱山》等发表散文,中短篇小说,曾获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表彰,曾获由中国旅游报,中国网等举办的“天柱山散文大赛优秀奖”。
{责任编辑:初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