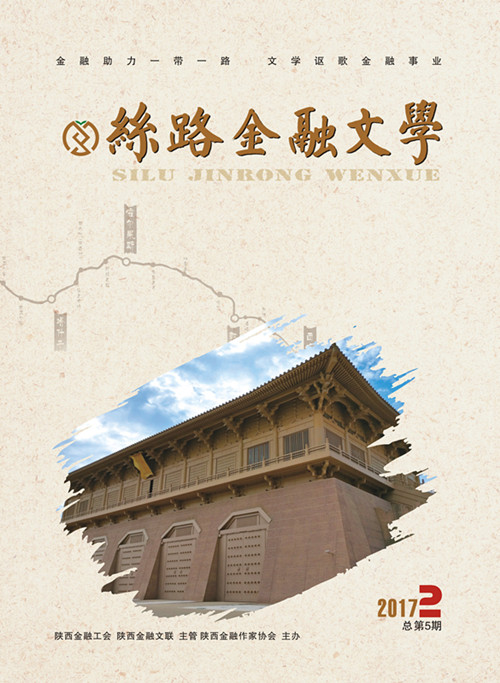从我记事起就畏惧我的亲房母舅——这个一脸麻子,长得凶巴巴的叫徐来狗的人。一听这名字有些怪,在十八里长岗,都说狗旺财,许多人家养狗,夜晚时分,大屋场狗叫声此起彼伏,上辈取名带狗字的多,大狗,毛狗,黑狗,狗财,狗富......乡间口头禅是猫来穷,狗来富。来狗喊我妈姐,是五服以内的姊妹,很亲的,我父亲那时是半边连的干部,家里缺劳动力,他帮我家种地施肥,进山砍柴,毫不吝啬气力。当然,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我妈也救济了他很多。然而在十八里长岗,怕徐来狗的人很多,他是以狠出名的,逼急了,连大队,公社干部都敢打,往死里打。
如果说当年徐来狗幸运地被解放军俘虏、收编、作战立功受奖光宗耀祖,而在朝鲜战场上死里逃生,却不幸被美国联军俘虏,则成为他厄运的开端。
小时候我挺纳闷,麻子母舅那样狠的人应该是战斗英雄,怎会向美国联军投降?不光是我,长岗人都认为!对于麻子母舅的狠,我是领教过的——那个封山育林年代,长岗两边偷砍树木的隔三差五,从徐麻子“看禁”后,很少有人盗伐,我有次放学回家看到外乡客不知深浅来犯,被打的鼻青脸肿,被捆住推搡着交与大队部。每当这时,大队书记伸着大拇指夸着麻子,都要奖励他一瓶“八毛一”老烧,嗜酒的麻子兴致更高,不分昼夜的在林子里转悠,希望抓到偷树的,换到酒喝。
一个暑假的下午,我和小伙伴们打听到麻子病了好长时间不能下床,便结伴到岗的东边扒丛毛柴,那时农家不光缺粮,也缺柴火,除了秋冬农闲时节青壮年到山里砍伐,平时都靠媳妇空闲、小孩放假、放学去周边扒,检枯枝。那天林子里无风,异常闷热,马尾松长的很密,落在地上的黄丛毛很厚,不大一会,我们光着膀子扒了一堆又一堆,准备装篓,不知谁喊了,快跑,麻子来了!林子里顿时炸开了锅,只见一光着上身,系白老布腰带的麻脸大汉手持棍棒从下方冲上来了,可能是病体虚弱,他跑的并不快,但虎威不减,我与小伙伴做鸟兽状逃散,我远远地望见很多丢下的篓子被喝了酒的麻子发疯似的踩掉,逃回家的我没少受到母亲的数落,田埂上,山地边不也扒到柴,非要去山上扒,你那母舅是猪,不懂人情世故,不讲情面,好端端一个篓子遭掉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母亲并不在乎我是否受到惊吓,坐在灶台心痛那只才买不久的竹篓!晚饭之后不久,家里的门被撞击了一下,母亲起身开门发现无人,看见了门角那只新竹篓。
对于徐麻子,我印象中最深的忌讳说他是俘虏,是投降兵,是怕死鬼。然而,做为战俘这一不争的事实把时光拉回到抗美援朝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麻子家在长岗的东边石坡村。日本鬼子投降那年初冬,在山坳地块里刨红薯,细细长长,穿着老布褂子的少年被一群带枪的悄悄包围了,像狗一样的保长带国军抓壮丁,麻子父母呼天抢地,眼看十五岁的大儿子被一根绳子绑走,随后几年音讯全无。
解放后次年初春,穿着一身草绿军装,帽带红五星的麻子回来了,他是战败被俘收编,参加解放厦门战斗,荣立二等功。麻子没死,麻子成了解放军立功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还听说就要转业了,一家人欢天喜地,然而归队不久家里就接到了信,简短的几行歪歪扭扭,大意是说朝鲜战局吃紧,所在部队即将入朝参战。
1950年11月,志愿军27军列入第9兵团,在朝鲜长津湖的冰天雪地里,与美韩多国盟军展开阵地争夺战。此时的北部朝鲜遭遇多年不遇滴水成冰的酷寒,麻子这帮南方入朝战士穿着单薄的棉衣,在炮火的掩护下,与装备精良的美军机械化师激战,盟军燃烧弹掀开的战壕里,很多战友冻死冻伤了,命大的麻子在死尸堆里剥下高鼻子带羽绒的棉袄棉裤套在身上,侥幸活了下来,他是机枪班班长,军事比武的神枪手,手持先进的捷克式转盘轻机枪,与战友发起了一波又一波冲击,收复着浓烟滚滚的阵地。麻子所在的机枪排成了美军飞机油汽弹轰炸的目标。那天黄昏,残阳如血,阵地陷落,炮弹的气浪把他掀翻了,血流满面,倒在死人堆里,昏死过去。朦胧中,他感到大队联军冲上来形成合围局面,在类似“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的稀里哗啦的狂叫声里,俘虏了自己一些伤痕累累的战友,抬走了尚活着的联军伤员,他还感觉到身边仅存的枪支弹药被联军收缴了。
夜幕降临了,整个湖面冻得似乎见了底,暮色中,像一条长长的带子,显得有些光亮——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位于赴战岭山脉与狼林山脉之间,由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向北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形成长津湖,最后注入鸭绿江。眼下,湖的两边是黝黑的山地,被炮火掀翻的冻土层,掩埋的烧焦树木,裸露的树根,散发着一层碳火味。 冬季长津湖,镶嵌在朝鲜北部如同夜明珠般光亮,又如同处女般清纯美丽的人间仙境,却遭遇了历史上惨烈的大兵团交战,湖面上坑坑洼洼,尸横遍野,一片狼藉。风夹着雨点雪花,从天边刮来,贴着湖面扑向两边的战壕,掩体。
联军打扫战场的脚步走远了,枪炮声仍然断断续续,阵地上散发着阵阵焦土味,血腥味。天阴沉着,上弦月,有些光亮,风“呜呜”叫,带着哨音,像刀子一样,顺着白亮亮的湖面刮来。醒来的麻子意识到四肢健在,抬起冻僵的手触摸了一下自己脸上的血块,头重如铅,不能动弹,头上套着死尸堆里剥下的加长贴耳绒帽,只露出脸,嘴,眼睛,尚存一丝气息,口干,饥饿,寒冷,他估计熬不过这个寒风呼啸的夜,就在他再一次在昏沉中咳嗽醒来时,发现左肩处有动静,一会有人翻身双手支撑勉强坐了起来,看对方土黄色裹着的大衣,感觉出是联军伤兵苏醒,显然,对方也发现了他,手无寸铁的麻子觉得自己死定了,索性闭眼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他感觉被身边人摇了一下,嘴巴里好像被注了碎冰渣一样的东西,是冰水?冰奶?还是毒药?管不了许多,死在今夜,做个饱肚子鬼吧!麻子张口嚼着,吸允着,渐渐缓过神,睁开眼,借助夜空微弱的光亮,发现了头戴棉帽,肤色如碳,嘴里吐着热气,身上散发着腥臊味的异国黑鬼军人,凭穿戴,麻子判断是土耳其军人,大多矮壮,穿戴笨重,在雪地里交战,摇摇摆摆,同狗熊一样。眼下黑鬼正吃力地侧着身子,拿着水壶嘴抖动着,撬着他的嘴巴。 显然,伤兵腿部受伤不能动弹,他颤抖着接过了水壶。此时,伤兵嘴里混胡不清叫着,解开棉袄内扣,从里掏出一块有些余温的肉疙瘩递了过来,麻子拿住颤抖着塞进嘴里,是牛肉干,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后方补给被炮火切断了,连日来,他们只能从联军死尸中寻找罐头压缩饼干等食品充饥,他强打精神,以微弱的求生力量,一滴不剩嚼完了尚未冻硬的牛肉干,并伸出舌头舔着手上的余味。
夜深了,麻子的体能得到了一些恢复,他吃力地扭动着身躯,为的是不让自己睡过去,或冻僵,抬头看了一下天,约莫子时,心里盘算着必须趁天亮前逃离寻找部队,否则夜晚睡过去会被冻成僵尸,即使不死,天亮时也会被联军抓俘虏,眼下只有弄死这黑鬼才行,否则他要掏枪的,联军装备补给要高出志愿军许多,前期麻子翻寻尸首找食物时,发现大都配有手枪匕首,他下意识触摸了身边的石块,眼下他完全有把握砸死这军人,他在悄悄等待时机,是弄死他?仇恨,感激交织着——这晚如果遇上别的联军伤兵也许没命了,这黑鬼还有人性,反倒救了自己!他放下石块,选择了躺下假睡。
朦胧中,麻子回到了那苍凉满目的家乡,为了活命,随着小脚母亲,带着打狗棍四处讨饭。记得离长岗不远处有个小寺庙,供奉着一尊土黄色的菩萨,两边点着香油灯,忽明忽灭,像鬼火一样,中间的花碗常有一点半生米饭。那天实在饿急了,刚进来还没磕头,就抓起米饭塞进嘴里,被随后赶到的母亲打了一闷棍,跪在菩萨面前磕头谢罪,以后的日子里,饿了就往庙里跑,帮庙里风烛残年的老僧端屎端尿,老僧捏紧裤带,省出一口喂养着他,说这孩子命大,是菩萨保佑的......话好像应验了,抓壮丁在安庆上船,行至江心遇风浪,船折了,掉进江里的新兵死伤过半,他紧紧抓住了缆绳,被拖上船。在被解放军俘虏前后,麻子已记不清参加了多少场战斗,在刀尖上绕道,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自己却无大碍,死里逃生,这就怪了,是菩萨在冥冥中保佑着.....眼下,伤兵呻吟着,发出了呼噜声,他悄悄爬了起来,双手在四周摸索,感觉别在腰上的那枚手榴弹被震落了,就在身子底下,摸到了,揣进了怀里,这是一枚光荣弹,是机枪班战士最后留自己用的。他拼尽全力,双手支撑着坐起,再踉跄站起来,一扶一拐逃离了,不多远,就发现了联军的营地,篝火,睡袋,炮群,他只得反方向走,只要遇上交火的枪炮声,就能找到部队,然而天亮时,被迎面而来的一队高鼻子蓝眼睛的巡逻兵发现,麻子又一次闻到了香水腥臊味,几支枪口抵近了,说时迟,那时快,他手伸向了那枚别在腰里的手榴弹扣环,眯上了眼睛,没有爆炸,是哑弹,鹰钩鼻子“哇哇”叫着,嘴里吐着热气将他扑倒在地,雨点般带着棉套的拳击得他眼冒金星,麻子差点昏死过去,被提起来捆住了双手......
中午时分,麻子被绳子栓着,押上装满战俘的美军卡车,然后再与其他兵用绳头拴在一起,尽管大多不相识,但都来自祖国的不同地方,大家相互点头示意。多辆卡车在断断续续的枪炮声中,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走了几个小时,到了美军一个临时俘虏营。
荒凉的河滩上,这里虽然没有长津湖的酷寒,但仍是雨雪交加,寒风刺骨。麻子与战友吃的是带着沙粒的大麦掺高粱饭,每餐只有一个小饭团,没有菜,战俘们时刻在饥饿状态中,大多穿的衣服仍然是志愿军装,胸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符号却被撕掉。最难熬的是夜间,河滩上只垫一块草席,盖的是一床相当薄的带着血腥味的旧军毯,大家挤在一起,互相以体温取暖,度过漫漫的寒夜。
半个月以后,美军对河滩上的战俘进行了清理,伤重不能站立的被抬走,说是治疗,其实全被活活丢进了冰河里,其余的被押往南朝鲜巨济岛集中营。
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正规集中营,也被称为战俘岛,四周是茫茫的大海,天连着海,海连着天,海水日夜拍打着礁石,随风带来阵阵腥味。被俘的两万多志愿军和六万人民军战俘全被关在这里,由三层铁丝网围着,四个角落都有高达二十米的岗楼,架设的探照灯、机关枪口对着帐篷,一直延伸到岛的边缘。战俘们每天都被美军吆喝着去搬运海滩上堆积如山的粮袋和战备物资。春去夏来,冰火两重天。太阳火辣辣地晒着,海滩上沙子被烤的发烫,亮晶晶的,海水带着热浪在疯狂地冲击着海滩,搬运工地上,麻子见不少战友都中暑晕了过去,不但没得到救治,却被美军活活丢进大海……
历时近三年,这场血与火的战争终以狂妄的美国联军被中朝军队赶出北朝鲜,退出三八线以外为终结点。 1953年7月27日,跌宕起伏的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字,而作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的谈判也进入最后阶段, 美方对岛上的中国战俘强制实施“遣返志愿甄别”,将志愿军战俘划分为“愿回大陆”和“要去台湾”,分别关押。在“志愿甄别”前夕,混入中国战俘营的国军特务采用哄骗,威胁,殴打,在战俘身上刻字,枪杀等一切手段阻止我被俘人员表达回归祖国志愿。
麻子面对着隔离关押,高音喇叭喊话,提审胁迫......他坚决要求回家,为父母养老送终。遣返的前夜,整个巨济岛战俘营被探照灯照的如同白昼,延伸到海的深处。一处处如同蒙古包,又如同灾后临时撑起的避难所,左边是胁迫去台湾的战俘营,右边是归国俘虏帐篷,中间是签字桌,围坐着不同肤色甄别人员,两侧的翻译官忙前忙后。这些出生入死的中国战士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做着最后的选择,他们被荷枪实弹的联军包围着......麻子被打的鼻青脸肿,奄奄一息,最后时刻,腐着一条腿的他,像一头受伤的野狗,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又跌倒,拼劲想支撑着起来,已无回天之力,在联军高鼻子蓝眼睛的叽里哇啦的哄笑声中,他在地上爬着,朝着归国的队列,一路血迹斑斑,当美军拉响枪栓的那一刻,他被一群眼里喷着怒火的战友们护住了......
从1954年1月中旬开始,数千名被遣返的衣衫褴褛的志愿军战俘分批乘火车返回祖国,归来者是从两条铁路线汇集到辽宁昌图。昌图是辽吉线上的一个县名称,在沈阳以北约120公里,位于铁岭与四平之间。这里组成了志愿军被俘人员管理处。最初的日子是火红的,首长接见,慰问团演出,女学生献花...... 归管处同志说在这里生活与学习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得到安置,回到祖国大家庭吃的嗝饱,穿得暖和,战俘们常常含着感激的泪花。
好景不长,这一切都消失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了“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文件,据说归管处对战俘上报处理安置的材料挨批了,犯“右倾”......如是,敞开的归管处大门关上了,战俘们在里面开始学习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标准,学习刘胡兰,赵一曼,江姐......然后开始控诉交代”。领导的话语变了:你们的功劳祖国人民知道,现在是你们向人民讲清问题的时候了。于是,当年在集中营带头英勇斗争的战友们先交代:与共产党员标准比,与死去的英雄比,差的很远。从被俘为啥没有“以死尽忠”,讲到“接受敌人的审讯,就是向敌人投降......他们讲的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交代了一次又一次,自我上纲上线越来越高,他们虔诚地涂抹着自己越来越黑的形象,直到最后,一些人连自己都吓呆了,这不是叛国投敌吗?
麻子在接下来的互助,启发引诱下,说出了自己死而复活的奇迹,说出了那个土耳其士兵喂送食物的经过,诅咒那枚该死的臭弹......事情闹大了,他被关了三天禁闭,要求交代与敌人来往的动机......最后,没有负伤被俘,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成了投降行为。
志愿军归管会对徐来狗的结论是通敌投降,取消军籍,一纸遣返通知书,把他发配回乡。
冬天来临了,麻子穿了一件褪色的军棉袄,背着铺盖,如同一头丧家犬,狼狈地回到了家乡十八里长岗。
当初,这些可怜的俘虏兵都是带着大红花、肩负着亲人和祖国的希望、踏着欢送的锣鼓点走上抗美援朝战场,如今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独自往家走,其心情无法言表。离开昌图前,很多人提出去北大荒或者去下煤窑,但都没有如愿。
看了盖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归管会鲜红大印的遣返通知书,公社武装部一个瘦长子脸色有些难堪:徐来狗啊,徐来狗,狗忠实于主人,狗不嫌家贫,你配不上狗的称呼,应该是一头猪!都说你是战斗英雄,你怎么向美国佬投降呢?怎么还通敌呢?你俘虏回来没被部队枪毙算你小子命大,你替家乡丢脸哪!回家吧,等候组织处理结论!说着看着,容不得麻子辩解,干部鄙夷地将遣返书揉成一团扔到了麻子脚下,随后又捡起摊开装进了档案袋。
麻子木木地背起铺盖,转身朝着家的方向,不知走了多久,到了长岗东边的一处茅草屋,门开了,麻子一头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苦啊,我该死啊,我丢脸哪......小脚母亲眼圈红了,伸出干瘪的手,颤巍巍地拉起了他,走到锅台边的碗柜,拿出一只蓝边碗,用勺子在青色瓦罐里挑了几勺红糖,冲上茶水,搅拌着,吹着热气,端到他面前。麻子坐在一条已经褪色的红漆凳上,伏在吃饭桌上抽泣着。一直坐在桌边的父亲脸色铁青,闷头嘬嘴“咕噜,咕噜”抽着水烟筒,许久,过足了烟瘾,抽出烟壶里铜烟嘴,在桌沿磕着烟灰,发话了:你把这碗糖水喝了,没在战场打死,被俘虏了也好,回来还是一条性命,像猪像狗一样活下去吧!说完,把红糖水端到了大儿子嘴边,麻子张开嘴,眼泪掉进了碗里。可不,红糖水可不是随便喝到的,一般招待来客,媳妇坐月子才有。
徐来狗在朝鲜战场被俘虏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有叹息的,怒骂的,讥笑的,但更多的是同情,夜晚,乡邻三三两两来看望龟缩在屋角的麻子,我母亲带去了一双布鞋,一把挂面,一袋苞米谷。
五十年代末期,东边的长岗原来有一处大屋群,住有十来户人家,麻子住东头,西头住着他的父母与弟妹。在十八里长岗,弟兄成年后分家,老大住东头,东头为大,父母都跟老小过,住西头。麻子返乡多年后,父母为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儿子找了一房地主成分、矮个、兔唇的儿媳,总算有个家。
长岗有句谚语:走运发财门板档不住,倒霉屋漏偏遇连阴雨。回家后的徐麻子被定性为“坏份子”,在生产队被当做“五类份子”监督生产,随着队长出工哨声,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那风起云涌的岁月里,麻子成了乡村运动被审查批斗的对象,甚至连他的家人都受牵连,老二旺狗的孩子升学都没资格。像一只丧家犬,他苟延残喘地过着,然而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与旺狗穿着蓑衣,用板车将难产的媳妇盖着雨布,拉到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由于凑不齐手术费,拖延中,媳妇下部大出血,顺着病床流到地下,医生抢救已迟!麻子痛不欲生,踢掉了卫生院大门的玻璃,抱住媳妇发疯地捶胸嘶吼着,头捣地磕出了血,他说自己是在战场上打死的冤鬼太多找岔子,遭到了报应。
老婆走了,带走了他的血脉。几年后,麻子父母也相继离世,家的氛围渐渐离去。长岗人看到,麻子将老婆葬在离父母不远的一块坟地。新坟培土后,他常常在坟沟里过夜,有时半夜伏在坟头狂叫,怪吓人的,像得了精神病一样。不听人劝,不要人拉,白天仍在下地出工,情绪一度低落,瘦得皮包骨,几乎不说话,没有家就没有牵挂,没有顾虑,他变得不像以前唯唯诺诺,夹住尾巴做人,甚至有些狂躁,逐渐对大队干部像唤牲口一样做义工产生抵制情绪,以往夜晚放露天宽银幕电影,都是他和几个地主富农布置场子,剧终收摊子,他力气大拖着满满一板车的器材,汗流浃背......对于那些频繁的批斗,陪斗,已显得憋不住了,他如同一头钻出牢笼的狼,在恢复自己的野性,蓄积待发!终于在一次批斗会上发作了——
大队部土台一人多高,半个篮球场大小,是为唱样板戏搭的,也可布置放露天电影,台下是一大片容纳到数百人的开阔地,特别适宜开群众大会。麻子和一批“五类份子”又一次被手持红白棍的红卫兵按着头,从侧面沿着石坡上台,台下是戴着麦草帽的从四面八方涌来,冒着汗味甚至是掺杂着狐臭的男男女女。五月天,插秧正忙时,广播里播送着提高警惕,防止一小撮阶级敌人复辟变天的紧急通知,村头墙壁上几乎贴满了不同颜色的大幅标语,“打到地富反坏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以往批斗,麻子头是低的,由于个子大,尖嘴猴腮皮包骨,脸斑斑点点,一看就像坏人,每次选他站中间,是大队书记的用意,容易激起群众的联想与愤怒,激发会场的批斗气氛。
大会开的声浪迭起,台上群情激昂,台下振臂高呼。这次批斗会麻子头被按了几次却是抬的,目光有些凶恶的注视着台下。这还了得,想造反了不是?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傻大个接过红白棍,对着他的后背狠狠劈下,麻子痛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当棍棒再次落下时,他本能地抓住了,一把夺过来,拉开架势,怒目圆睁,闪电一样朝大个子腿部扫去,傻大个躲闪不及,惨叫着,一头栽倒,上来的几个被发了疯的麻子打得“哇哇”乱叫,抱头鼠窜。
台上台下炸开锅一样。
麻子用过了力,体力不支,被拥上来的人摁倒了,挨了一棍子的民兵营长踩住头,帮手用麻绳套住颈部,像捆粽子一样绑了个结实,闻讯赶到的派出所干警把他像牲口一样倒拖着,抬起来甩进警车后备箱,关上门呼啸着离去。
一个月后,被剃了光头的麻子从看守所回到了长岗,县城离家有四十里,走了四个小时,累了,坐一会,渴了,趴在塘堰喝一饱。晌午时分,弟弟旺狗远远望见岭上的他,踉踉跄跄的,走近了,拉着到家,弟媳小满赶紧从从竹碗柜里拿出蓝边碗,盛满野菜煮饭,看着他狼吞虎咽吃了。这种蓝边碗比一般碗大,是劳力吃饭用的。吃饱了的麻子打着嗝,坐在门槛上,接过弟弟递过来的“丰收”牌香烟,大口吸着。哥,你太较劲了!岗前岗后挨批的人都不像你自讨苦吃,胳膊拎不过大腿,是这命有啥法子?你是“坏份子”怪谁?哪个叫你战场当俘虏呢?又有谁叫你说出那个外国士兵救了你?公社王书记与小满还有点沾亲带故关系,划成分没把你定“反革命”算你幸运了。弟弟望着瓦屋梁,缓缓吐着烟雾说着......
然而半年后,麻子惹了一桩更大的事,轰动了长岗。
一个人过日子,白天上工,逢早晚阴雨天,冬春季节到山上张弓捕些野兔,夏秋去塘堰叉点乌龟老鳖,田间钓点黄鳝,买了换油盐,有时也送点隔壁的弟弟,山里的妹妹,虽然也缺些口粮,但日子凑合着过,锅台搭在脚背上,一人饱了全家饱了。
文革前,长岗很多人家都有猎枪,听长辈说以前是对付兵荒马乱的,后主要用来打猎。长岗独特的山林气候,黄土岗,洞穴多,野猪,野兔,野狗,野獾,黄鼠狼常出没,岗前岗后几个人组成围捕小队,常有收获,最大的诱惑是这些动物的毛皮值钱,当地供销社土产门市部收,往往是将新鲜的野兽皮用竹条撑开四肢,挂在壁上晾干,据说还能出口换外汇。一张完好的兔皮可买二元,狗皮在三元上下,要知那时当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十几元,另外剥下的野味肉解馋,对于许多人家缺油盐、有的几个月沾不到一点荤腥,是一种难得的补充!一时间这些动物差点绝迹。文革中,猎枪被收缴,野猪野兔又出现了。麻子是在山里妹妹家找到了一柄锈迹斑斑的鸟桶抢,带回家拆开擦洗、组装,不知从哪弄到一些铁砂,火药,偷偷躲到自家靠山边的菜园地里,调试瞄准、弹药发射。为避人嫌,那个初冬之夜,他用破衣裹着枪,偷偷摸到了岗对面叫做公主岭的山坳里,打着电筒,寻找野味踪迹,一夜下来,只在树杈间找到一些鸟窝,鸟惊的“扑扑”飞走,麻子爬上树,一手拽着树干,摸到毛茸茸嫩鸟凑近看着,然后小心放回鸟窝,摸到一些鸟蛋,塞进挂在颈上的包里。
第二天下午,在枯黄芭矛丛生——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沟里,成熟的野柿,野果被风刮得零零散散,动物啃吃的残渣随处可见,还有那一滩又一滩像黑豆粒一样的粪便。啊,是兔窝!芭矛丛里,他轻手轻脚,猫着腰,分明看到了那几只咕噜着黑眼珠,涂抹着夕阳余辉的金黄色野兔,耸着一双机灵的耳朵在东张西望,枪响了,带着硫磺味,弥漫着,狂奔的一只野兔倒下了,“嘶嘶”尖叫着,流着血。山谷里,惊动了山鸡,山雀四散奔逃,麻子左冲右突,是那样的矫健,那样的勇猛,端了一窝又一窝,打了一只又一只,仿佛当年端着转盘机枪,横扫朝鲜战场上的美韩联军!那喷洒着铁砂子,杀伤力有十平米大小的火药鸟桶枪,“喷”,“喷”响着,被打死打伤的野兔野鸡野鸟,足有半麻袋,他等到太阳落山后,用绳子捆紧袋口,然后用两根草绿色松紧帆布带套住麻袋,蹲下来再套在两肩,起身虽有些沉,但麻袋牢牢的贴在后背上,这带活扣的松紧帆布带是入朝参战背行李的,牢固实用,没舍得丢。麻子沿着夜色背着猎物走了大半宿,不时用手抹着额头上汗,到家时,已是鸡叫头遍了。
{责任编辑:初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