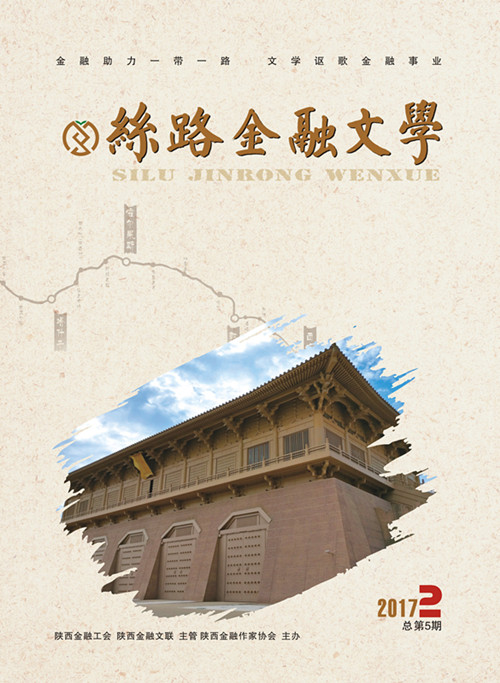丝路金融文学网讯(记者 云鹤)3月19日下午3点到5点,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新书《西部向西》签售会在西安小寨新华里举行。《西部向西》是肖云儒先生近三十年研究西部文化的一本散文及小说合集,作为丝绸之路丛书中的一本,我们将可以从中了解到肖云儒先生深厚的西部文化情结,以及个人文化性格的发展脉络;了解西部、西部以西以及丝路精神对当下的影响和贡献。


签售会上,肖云儒先生回答了主持人和部分与会嘉宾有关西部、西部文化以及他的个人身世和学术方面的提问。“陕西朗读者之家”陈爱美等陕西播音界名流现场朗诵了《西部向西》中的部分章节。现已76岁高龄的肖老仍然思维清晰、反应敏捷,精神矍铄,现场答问后,顾不得休息,又投入到为读者售书签名活动中。



缘于共同的“丝路文学”情结,记者在请肖先生为自己购买的新书《西部向西》签名的同时,提出可否为陕西金融作协主办的《丝路金融文学》杂志和网站写一句话,当肖老通过手机看到“丝路金融文学”网页后,欣然提笔写下“丝路金融文学深耕远行”,寄予期望和祝愿。

【作者简介】
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书法家、教授,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德艺双馨艺术家,中国文联委员,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会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政协委员、评论家协会主席。著有评论集及散文集《民族文化结构论》《八十年代文艺论》《独得之美》《独步岚楼》《黑色浮沉》《美》《对视》书系五卷、《国格赋》《黄土•红土•绿色的歌》《长青的五月》等。
肖云儒在各公众媒体上热情地为西部为陕西做文化推介。他在央视的"精彩中国"、"魅力城市"等大型宣传活动中,在凤凰卫视和各地电视台的《纵横中国》《开坛》《黄帝陵大祭祖》《金庸华山论剑》和《城市名片》等栏目中,乐此不疲地解读西部文化,宣传西部,并先后为西部的十几个城市做文化代言人,被公认为西部的文化大使和形象代表。
寻找肖云儒
《时代人物》记者/葛少欢 钟艺
影像的魔力在于,它能把你的人生定格在某个特定的瞬间,我们因此不再老去。它们得到了时间的特赦,把百年真相留到今天。
自头天晚上开始,肖云儒的手机和座机有个神秘的电话响个不停,那组电话数字一会儿比一般的手机号码长,一会儿又比座机号码还短。刚刚读过神秘手机诈骗钱财和吸走信息的报道,肖云儒很是警惕,不敢轻易接,不停的电话铃声又让他心里放不下。咨询儿子,儿子说接可以,只是不要主动回过去。
在第N次摁掉电话后,急促、清脆的铃声又一次鬼使神差般响起来。肖云儒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环顾了一下四周,准备着或将发生的一切,拿起了话筒。
“你是肖云儒吗?总算找到你了!我是谁?你肯定忘记我了!你记不记得我母亲,她姓钱,是武汉的。”
“你忘记了吗?你那年在人民大学上学,暑假回南昌,我们两家母亲安排你在武汉玩了两天,有意撮合我
们,有那么一点儿相亲的意思。我带你逛得武汉呀,我是高屏。”一位女士坦诚而急切的声音,容不得他插进半句话。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就在找你,找苦了,甚至给火葬场打电话,想得到你的消息。网上也找了好久。后来辗转找到了你的单位,可算是找到你了。我这里有二十多张你母亲的旧照,一直想转交给你。”
肖云儒被拽回悠悠的时光隧道。
高屏寻找着肖云儒,肖云儒却在寻找母亲,寻找母亲留在世上的任何一件微小的物品,甚至她的气息……
唉,两家的母亲如果健在多好,今年都是整整100岁了!
初秋的夜凉气逼人,肖云儒感慨万千,久不能寐。是啊,两位母亲,最要好的“闺蜜”、几十年的挚友……他一骨碌从床上起来,裹紧睡衣径直走向书房,去找老照片。
脑海里满是母亲的一颦一笑,尘封已久的记忆像是稀释的硫酸,灼痛着他的心……
第二天,高屏便从美国将她保存了半个世纪的老照片和信件发了过来,邮件的题目全是人生的苍凉:《终于找到了你》《劫后余生》《人生长河点滴》……“见到母亲的亲笔信和照片,我一看再看,多熟悉的字迹!那笔画唤醒了儿时的画面,复活了青春的信息。关于她,关于我,关于你和你们,关于那个时代……”
高屏的寻找,高屏的出现,令肖云儒好久不能平静。脑海里想象着她艰难寻找的每一个片段和将来越洋重逢的喜悦。
100年,两代人,母亲与肖云儒的人生活脱脱是中国近百年的一部个人影像史。
“找了二十多年,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
原本的相亲之言,当然只是两位母亲希望延续友谊单方面的愿望,年轻人自有自己的想法。
高屏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热情、率真、能干,但此后命运之坎坷,让肖云儒始料未及且痛惜不已。从高屏发来的倾诉大半生经历的长信中知道,她1965年大学毕业即考上研究生,迅即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在一夜间把这位天真无邪的少女推向深渊。父亲高伯伯因是武汉医学院(即现在闻名的同济医科大学)院长,被作为“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死于非命。母亲钱姨在悲痛欲绝中被强迫下放到农村,患乙型脑炎而辞世。弟弟高迪在异地插队劳动。背着“不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恶名,高屏从北京被发配到广西,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爱人高光荣却被发配到北大荒离中苏边境只有百十里的小镇上。几年后,她才被允许自背铺盖千里迢迢寻夫结婚。儿子临盆时,又遇极度危险的难产。
受尽磨难的高屏一家,在粉碎“四人帮”后才有了转机。丈夫后来考上新时期第一代研究生,而后留学美国,组建ACAPS,CAPSL实验室,被选为美国IEEE,ACM院士。儿子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现在纽约当律师。
时间再倒回到上世纪90年代。高屏的弟弟高迪突然收到一个越洋电话,是个素不相识的人。陌生人说,当年他被指使去烧毁“走资派”高景星(高屏的父亲)家抄出来的所有“四旧”,包括日记、信件、照片、唱片,出于好奇,他读了高的日记和家书,实在看不出反动在何处,反倒为日记和信件中的亲情所感动。于是良知战胜了对极“左”的效忠,他悄悄把这些资料藏了起来。这位陌生人还回高家的物品中,就有肖云儒母亲的照片和信件。
“妈妈以她对好友的爱,小心保存了这26张珍贵而充满故事的照片。”高屏在电话里对肖云儒说。高屏重新买了影集,替九天之外的父母将这些时代的证物、友谊的证物保存起来。也是从那时起,高屏开始寻找肖云儒,要将这些照片“物归原主”。
“网络、电视、电台、学校、工作单位、火葬场,只要是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个遍,但自己在海外,与人家不熟悉,没有人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这一等20年就过去了。”
这些照片最早可追溯到1935年。经历了国、共几次战争的炮火,又经历了“文革”的浩劫。这些照片,再加上肖云儒自己保存的、也是在“文革”中失而复得的几百张老照片,通过一位知识女性的影像,反映了100年中前50年的社会面貌,实在珍贵至极。肖云儒还珍存了自己从襁褓一直到古稀之年的留影,一部个人化的百年史,便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都制成了电子版,发到了美国。
影像的魔力在于,它把你的人生定格在某个特定的瞬间,我们因此不再老去。它们得到了时间的特赦,把百年真相留到今天。
“你和你母亲的感情令我热泪盈眶。愿她在天之灵安息。那些留下珍贵记忆的照片,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父母的恋爱,他们的朋友,他们生活中那一章一章难能可贵的故事,都似乎要被淹没在红色的狂热风暴中,永无痕迹了,不料重又复活!”读了肖云儒写母亲的几篇散文,高屏在电子邮件里说。
“看到你发来这么多我没有的照片和信件,我真是非常非常感谢,感谢你的寻找,感谢你的执著。你让中断的历史重新接上了头。”
“第一次去婆家,得到20斤棉花”
肖云儒的母亲欧阳明玺是高屏从小熟悉的名字,“你母亲常把我母亲带回到那无忧无虑的青春岁月,这就是她们策划‘相亲’的缘故吧。”
其实,在此之前,肖云儒也一直在寻找。他的足迹踏遍母亲生活过的每一寸土地。
“四川是我‘遥远的背影’,我的祖籍;如果说人生是一幅画,四川就是我那幅画天然的底色。江西则是我心灵的底色。虽然只呆了17年,但真正怀念的是江西,那是我心灵的故园。”
1940年12月的一天,肖云儒出生在江西赣南的小城于都。四川广安的祖父在农村开酒作坊,小有积蓄,所以能够送儿子上大学。外祖父是知识分子,和鲁迅同一批去日留学,曾担任《中华大辞典》的编撰主任。父亲肖远健,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中共地下党员。母亲欧阳明玺,求学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鲁迅笔下刘和珍君的校友。

肖云儒母亲(右)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随着由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成的西北联大迁到汉中城固。当时西北联大只有教学楼,学生大都租房散住着。同学中,还有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妻子。陆定一的儿女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是肖远健。
父母在上世纪30年代“12?9”爱国学生运动中相识相爱,“革命加爱情”的模式很像小说《青春之歌》里的画面。婚后一度想去延安,行至西安,却受组织委派,辗转去了重庆,并顺道回了一趟广安老家。母亲说,她第一次去农村的婆家,刚见面婆婆就发给她20斤棉花,并嘱咐:以后家里不给零花钱了,你就用这棉花纺线织布,卖了零用。母亲是个洋学生,住了几天就去了重庆,把这当成乡村故事给同伴讲。
父亲的地下工作需隐蔽,母亲便在重庆一位官僚家做家庭教师,掩护父亲。几年后父母受命去了江西。长征之后,陈毅的部队留守赣南,父母在赣南游击队中从事教育宣传工作。1941年,父亲因肺结核病去世,留下1岁的孩子。无奈的母亲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回到外婆家。抗战胜利,他随外婆一家坐一条乌篷船,在不舍昼夜的橹声中,北上南昌。在那里开始了母子相依为命的生活。
“半辈子”的女校长
几十年来,肖云儒竭尽全力寻找与母亲有关的人物。广安、于都、南昌、临川、北京……他的脚印迭印着母亲的脚印。“找到了母亲的很多学生,大都八、九十岁了,只要回忆的灯一在脑海中点亮,生命重又显出亮丽的色彩,变得健谈,表情丰富,不时发出笑声。“我到母亲曾任教的女中校史馆,她的照片挂在冰冷的墙上。当年的老师大都去世,只是有些房子还留着。物是人非呀!”
新中国成立前几年,母亲曾在美国教会办的葆灵女中任教。蒋经国暗恋的章亚若就是这所学校的校花。新中国成立后,母亲代表新政权从美国人密斯孔手中接办了这所教会学校,改名南昌女中。母亲搞了半辈子教育,后来担任了江西省图书馆馆长、省妇联副主席的职务。
母亲要同时以父之严、母之慈,承担起教育儿子的责任。“你不能没有出息”这是她的口头禅。肖云儒曾写道,“对我的功课近乎残酷的督察,每每惹外婆暗自流泪。至今想来,仍然感觉到一种甜蜜的战栗。我甚至恨过她,又终于懂得能够从小接受大松博文式的教练,是我的造化。那远低于家庭经济水平的简朴,教我简朴,那不完成作业不能睡觉的训令,使我勤奋。铁器是在铁砧上锻打出来的。若是让一位寡母冷酷地锤打自己的独子,心里又该是怎样的滋味?”
肖云儒最早对于文学的敏感,却是来源于一场意外的生离死别。
新中国成立前夕,母亲在临川女中任校长,和他们在一起的三舅才15岁,由于不想上学,竟偷偷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母亲当时急火攻心晕厥过去。醒后即刻领着校工前往新兵集训地,准备用绳索强行捆回来。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三舅从此去了台湾。外婆的悲伤、外祖父的叹息、母亲的内疚,几十年压在心头。五十多年的生离死别,成为这个家庭无法弥合的伤口。
肖云儒上中学后,在作文里记述了这件事,文章结尾,他以暗喻的笔法写道:“拂晓时分,妈妈才从新兵集训地回来,疲惫而无助地把我揽进怀里,我们都忍不住啜泣。东方已经现出微熹,天,就要亮了。”这篇作文被当做范文诵读。真挚的情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点燃了一个少年的文学向往,文学的种子在心里悄悄地萌芽。
孤独的母亲,常常晚上一个人听留声机。留声机不像现在音质那么好,嘎吱嘎吱的,像在母亲心上划着一道道伤口,给年幼的他带来莫名的悲哀。
而肖云儒最幸福、最神气的时刻,便是母亲背着外婆一家人,领着他上街去吃肉饼汤。母亲在一旁静静地端详着狼吞虎咽的孩子,眼里全是爱恋。对于母与子,这份爱都是独享的。
“写了一半的信,吃了一半的蛋糕”
去年他们一家三代专程回南昌给母亲修了墓,今年呢?“我们会回去给她老人家扫墓。每想到她一个人躺在阴冷的山上,便内疚、自责。我得回去给她暖暖心。”
“老妈去世时才52岁,我总悔恨自己不是女儿,生前不太会跟她谈心,听她的倾诉。这些年生活好了一点,便悔恨老妈孤苦伶仃,一生短暂,什么都没赶上!好悔呀。”这么多年了,现在还总是梦见她。梦中用家乡话交流,母土,母语,仿佛跟母亲还有脐带连着一样。“我经常有种感觉,她就是佛,总在云端注视着我。我们之间不只是血缘关系,她更是我精神的一个标尺,人生境界的一种标杆。母亲和母土、母语一样,是我们心中的信仰啊。”
时间用一种独有的方式在你的记忆中筛选,肖云儒曾大哭过两次,都是因为母亲。
上大学时,母亲因高血压眼底出血而病危,当时长途电话特别难打。他在北京东四邮局等了一下午,悬着的心绞痛着。当听到电话里说“人不要紧”,肖云儒大哭起来。
1964年早春,江西省开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发言的母亲,猝发脑溢血当场离开人世。身处异乡的肖云儒闻讯后,暗自躲在单身宿舍,嚎啕大哭。待肖云儒从西安日夜兼程赶回南昌,只在太平间见了母亲一眼,便径直被接到中山纪念堂的追悼会上。
人来得很多,大厅外面站满了母亲的学生。亲属的位子却只孤零零地站着肖云儒一人,他是那样的孤单和凄凉。仪式按议程进行着,他脑海里却固执地想着躺在太平间的母亲。化了妆的母亲显得有些陌生:闭着眼,闭着嘴。丧事还算体面,江西省出面料理,《江西日报》登了消息。这些外在的哀荣更反衬了他心底的寂寞,“我再也没有老妈了!”
从墓地回来的路上,霏霏细雨像母子执手相看泪眼婆娑。“她一辈子孤单,如今又把她一个人留在山上,不能陪我苦命的妈!”她没有看到儿子结婚,没有看到孙子,常人的天伦之乐她都没有享受到,在战乱、运动中度过了一辈子,生命就这样像流星一般划过了!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灰暗的灯光下,桌上放着写了一半的一封信,天呀,那是给儿子的!旁边有块咬了一半的蛋糕。单人床一侧堆着母亲最后几年写得七八部中国女性系列历史剧。从班昭、王昭君、李清照到秋瑾。肖云儒又一次失声痛哭。
27岁守寡,52岁辞世。这是怎样一位凄凉的女子?
1992年1月,肖云儒在一篇名为《母亲——自序<民族文化结构论>》的文章中,催人泪下地描写了母子间的深情:“半岁丧父,亦无兄弟姐妹,母亲终身守寡,将我拉扯大。我与她,她与我,都是唯一的,独有的。她携着我,我搀着她,脚印交织在人生路上。”这篇文章后来被选入中学语文辅导资料。
寻找一切与母亲相关的人,寻找自己的生命轨迹,寻找一段历史。幸好还有真切的影像,将刹那变为永恒,将过去了的那一代人、过去了的那100年,定格在我们的心中。
直到现在,肖云儒还常会重复着同样的梦境:“妈,你怎么还在这座城住着?为什么不来信?”“你好我就好啊……”醒来后,肖云儒总是黯然伤神于漫漫长夜。阴阳之间,为什么总是横亘着一道可望而不可及的透明的隔音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