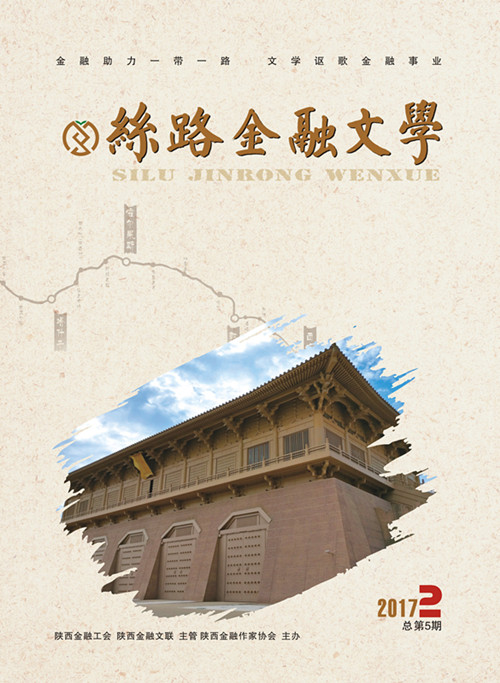西安因为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就有了城内城外之分。当地人认为,住在城墙里的才是城里人,住在城墙外的就是郊外人,无论近郊还是远郊。郊外人把进城叫“去西安”,令外地人十分诧异。城内东、西、南、北、大街笔直宽阔,公交车南来北往,交通便捷,生活设施齐备。而出了东、西、南、北大门,除了主干道两旁一家挨着一家低矮的铺面建筑外,再往深处走,不是临时搭建的民房,就是农田。相比之下,城内才像个城市。
从香湖湾到朝阳门不过15公里路,有33路公交车直达。大人们常“去西安”,我没去过。
“文革”时期的一天,离过年还有一个星期,我奶对我爸说:“你带俩娃到西安去,叫娃也见个世面。”我爸当时被列为“四不清干部”,时常接受批斗,哪有心情出去逛。我嚷着要去,我奶也劝他说:“出去散散心也好,不要老想窝火事。”我爸听了我奶的话,同意带我和我弟“去西安”了。那时候我7岁,我弟4岁。
当天晚上,我爸就把要用的粮票、钱装进内衣口袋。我兴奋得大半夜睡不着觉,想象着西安的样子:那里有很多高楼大厦,有色彩缤纷的霓虹灯、井然有序的车流,如电影里周总理访问过的纽约、巴黎,或者像北京、上海那样,与农村相比,就是天上人间。
第二天一大早,我爸抱着我弟,领着我到香湖湾车站等车。大约等了半个多小时,33路公交车才从新筑方向缓缓开过来。车上挤满了人,全程车票2毛五分钱一张,我爸给他自己买了一张,我们3人夹在拥挤的乘客中,摇摇晃晃地随车前行。在这之前,我到过半坡,对这段路的沿线不觉得新鲜,就低着头,任凭周围人如何拥挤。过了半坡车站,人少了些,我爬到窗口,希望看到没有看到过的景象。从半坡往西走,路变成了柏油路,路面也宽阔了,感觉车也行驶得平稳了,就是没有高楼大厦。路的两旁,偶尔出现的房子,也是平房。到了韩森寨,才看到三、四层的楼房,那楼房和路旁的树差不多高,是砖砌成的,丝毫谈不上华丽。再往西走,情形大致相同。我们从朝阳门外的搪瓷厂终点站下车,我爸抱着我弟、领着我穿过朝阳门,沿着东五路,走到解放路。
城里沿街店铺多数为二、三层楼房和平房,比较破旧,到处可以看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标语,与城外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行人多了,骑自行车的人马蜂般的成群结队,汽车并不很多。十字路口,自行车、行人、汽车同行,也不见拥堵。国营商店门前摆放着鞭炮、对联、样板戏年画,还有彩色气球,呈现出几份新年气息。
我们先到位于解放路上的珍珠泉浴池洗澡。这是西安市有名的国营大澡堂,顾客一落座,服务员就会端来一杯热茶。更衣休息室是个大房间,铺着白色褥子、床单的单人床沿墙壁整齐地排列着,床与床之间用床头柜隔开,衣服就锁在柜子里。一个人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条浴巾、一条毛巾,我们3人只能用我爸那一套。
走进浴池,一股混合着肥皂、脚臭、尿腥气味的热浪扑面而来,地板油腻腻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倒人。我爸裹着浴巾,穿着拖鞋抱着我弟,我一丝不挂,光着脚丫子,紧跟着我爸进去。中间大池子里,一个挨一个的人,悠哉乐哉地用毛巾沾热水往身上敷,额头、脸颊满是汗珠子,却很享受。四周淋浴喷头下,也是一个挨一个的人,你冲了我冲,我冲了你冲。有的几个人挤在一个喷头下冲,溅得满身都是肥皂泡沫。
洗完澡,我爸带我俩到黎明牛羊肉泡馍馆吃羊肉泡馍。里面食客众多,排着长队。开了票,我们就坐在凳子上等候服务员叫号。那服务员声音洪亮而个性,只在柜台里拿腔拿调地喊:“56号、57号……”,并不把饭给顾客送过来,叫到谁,谁就到柜台前自己端。
我爸端来两碗羊肉泡馍,他和我弟吃一碗,我吃一碗。半天没吃东西了,肚子经浴池热水浸泡后,像掏空了一样。那新鲜红润的羊肉、白生生的煮得软软的碎馍块,飘着葱花、香菜、粉丝的汤汁,还有微辣而甜的糖蒜,平生出一股魔力,勾引着我的食欲,嘴角竟溢出口水来。我贪婪地扒拉着吃,我爸嘱咐:“慢点吃,别烫着了。”
吃完饭,我们绕过钟楼往北走,在钟楼附近看见邮电大楼、人民剧院、报话大楼。这几座建筑是西安当时最高,也是最有品味的现代建筑了,但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华丽、优雅。接下来,我们去了革命公园,再后来,天就快黑了,我们又从朝阳门外的搪瓷厂乘33路公交车返回。
我奶问我:“西安好不好?”我说:“没有多少高楼大厦。”我奶迟疑地自言自语:“叫带娃进西安城,把娃带阿达(哪里之意)去了。”我奶又问:“看见钟楼了吗?”“看见了。”“那就是进城了。”我奶这下才放下心来。
那时候,工农一家。我们村里的人,日常洗澡都去附近工厂的浴室,那里只是更衣室没有珍珠泉讲究,其他条件还不错。早先去过的半坡,也就在纺织城附近,与城内的景象相似。第一次去“西安”,除了觉得羊肉泡馍好吃外,没有什么新鲜感,朴素而灰色的西安城,未能满足我对城市的幻想。后来,我在城墙西南角上了西北大学,在城内二府街市政府财贸院参加了工作,以后又分别在纺织城、小寨居住。对西安太熟悉了,便觉得沉闷而无聊,随产生了去沿海工作的念头,想在那里感受不一样的地貌风情。那时候,海南特区刚开发,我就随着南下大军去了海口市。海口的椰风海韵,着实让我感到新鲜而惬意,但很混乱,找不着喜欢的工作,又返回大陆,去了另一个沿海特区——厦门。厦门被称为华夏之门,是著名的侨乡,隔海与台湾相望。在鼓浪屿的轮渡码头,随便找一个人和你交谈,都会说他的什么人在台湾,那神情是黯然落寞的,眼睛直直地望着远方的海面。厦门,这个多情、浪漫,略带忧郁的城市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很快在这里找到了工作,但终于未能去,成为一大憾事。后来,我结婚了,那颗漂泊不定的心,也渐渐地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审视西安,才发现西安并非那么灰头土脸,只是展示了与厦门不一样的风采。她古老而年轻,质朴而时尚,典雅而妖娆。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当你和她融为一体的时候,你的眼光只会看到他人,不会看到自身,也就发现不了自身的美丽,而外来西安的旅游者们,则会细细地感受她的魅力,就像我感受厦门一样。
农村人向往城市,小城市人向往大城市,内地人向往沿海,大城市人向往国外的城市,是人们很正常的心理特质。当愿望满足了以后,就会习以为常,乃至熟视无睹。正是这样的心理特质,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一味地追求城市外在的差异,就会像一朵浮萍,没有根基,难以得到心灵的归属感乃至幸福感。
我的一位朋友,曾随女儿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居住。初到第一个月,女儿陪他走遍了旅游热点,还算兴趣盎然。到第二个月,就有些麻木了。女儿上班后,他一人住在别墅里,遥看碧草蓝天,除了清新的空气能带来一丝安慰外,落寞、孤寂让他困苦难耐。到第三个月,他实在住不下去了,执意要回国。他说,我宁愿在国内呼吸不清洁的空气,忍受不合理的纠葛,议论烦心的国事家事,也不愿意住在他国,因为,我不是这里的主人。
人是社会性的,无论你住在哪座城市,只要住久了,就是这里的主人。如同一棵树,长的久了,根系就复杂了。你会熟悉这里的大街小巷,适应这里的气候、饮食、风俗、习惯。你的语言、情感乃至思想会融化进去,这里变成了你的一部分,你会以她为荣,甚至袒护她的缺点。她发达了,你会为她欢呼;她落寞了,你会为她忧郁。外面的城市,哪怕再美好,也只是一道风景,可以游览,不可以久留。我生长在西安,也就和她融为一体。她的住民大多与我相似,秦腔秦韵,淳朴厚道,脾气耿直,多食面食。喜欢西安,与她是否有千种姿色,万种风情没有直接的关系。她低矮的时候,我欣赏她的淳朴;她高昂的时候,我欣赏她的飘逸,只因为她包容着我的躯体和灵魂。
她,就是我心中的那座城。
2015年3月9日于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