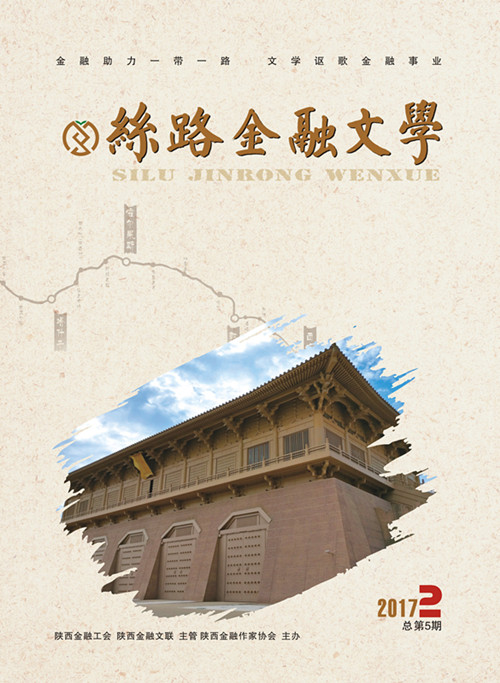晚饭后,正在书桌前抄写李白的《行路难》诗句,二哥打来电话,说六爷去世了。
我听了心里不由得惊了下,随即又平复了。六爷九十四岁高龄了,去了也正常,可年岁再高,当一听到人去世了,心里难免犯咯噔,这就是人们对生命的敬畏!
六爷是我们村里张姓人家的一位老者,在他们那个大家族里面男子中排行老六。按照村里的辈分,我们家族在村里辈分低,我们叫他六爷。对六爷有记忆是我上初中时候开始,在我家院子,会偶尔听到六爷高喉咙大嗓子的喊话,那是在找我的父亲,每一次说了些什么我也没有留意,所以也就没有啥记忆。可对六爷这个人却有种不一样的感觉,六爷面冷、急躁、声大、话少。他每每找我父亲,都是直撞进我家院子,人还在头门口那如洪钟般的声音就已经穿越到我家后屋,随着声音的起落,走近的便是高大魁梧的六爷,我家桩子很长,从大门口到后屋大约三十多米,我们家大小人就都听到了六爷的声音,母亲会第一时间给父亲说,快去看,六叔来了,看说啥。六爷一看见我父亲,就提着嗓门机关枪般的语速说话,父亲对六爷的寒暄、问候如烟似云,六爷压根就没在意,也不应答,就匆匆离开了我家。所以我老注意不到六爷找我父亲说了啥,却是全身心地关注了六爷那个让我觉得怪怪的神情,他喊我父亲的声音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急促、宏大、厚重;他和我父亲对话的表情让我对他产生了好奇,没有闲聊话,直奔主题,也不理会我父亲对他的嘘寒问暖,我老觉得六爷是个奇怪人,更不解的是父亲咋就和他还这么要好。
记得有一次,六爷又是在我家院子喊话,他喊我父亲的名字,“龙翔......”苍劲的声音直冲云霄,这一次父亲是去单位上班了,没在家,我出来应答:“六爷,我爸爸没在家......”,一听说我父亲没在家,六爷转身就往外走,我还一直在给他说着没说完的话,可是他已经走出了院子,根本就没再听进去,更不问我父亲是去了哪里。我好尴尬,也很是纳闷。晚上父亲回家了,我就又气恼又好笑的给父亲说了中午的事情,嘀咕着六爷咋是个那样的人,根本就不把别人当回事,当时言语里对他表现出了不满。父亲却认真的说,额,你六爷那是个好人,直脾气,性子急,心好!我瞬间一脸的火,吓得再没敢做声,但凡父亲认可的人,那一定是不敢非议的。后来,听过父亲说的六爷的故事,甚是感动。
六爷生于1929年,小时候家境贫寒,家庭兄弟姊妹们多,年龄稍长点就被卖做壮丁。1949年六爷参加了解放军,参加过西北解放战争;1951年六爷加入了志愿军,跟随部队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六爷作战英勇,立过军功,后来政府给授予《人民功臣》牌匾,悬挂在他家门楣上,给全村带来了荣光!残酷的战争给六爷身体造成极大伤害,1953年六爷从朝鲜战场上下来回到祖国,被转业到地矿部,后就职于安徽331地质队,六爷工作上兢兢业业,一直以一个解放军战士的军人作风严格要求自己,多次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六十年代,六爷因病告老还乡,过上了少吃没穿苦不堪言的农村生活。我还记得,父亲说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下,语气里充满了惋惜,同情。我也情不自禁的扼腕长叹,六爷,一个战功赫赫的解放军,本该过上安逸的生活,享受好的待遇,却落得个和我们一样过着艰苦生活的农民。战争的电影我们也经常看,血粼粼的战斗,战场上的残酷,之前就以为是在演电影,现在活生生的经历了金戈铁马,纵横沙场激烈战争的战士就在我们身边,还时不时地跑我家院子来喊话,难怪他喊我父亲时的声音那么宏大,铿锵有力!一个英俊霸气、持枪驰马的军人形象即可镌刻在我的脑海,令我肃然起敬!以后,我每每看见六爷,绿军装便瞬间浮于眼前,那一身沾满尘土、污渍遍布的粗布衣泡影般消失了。本就高大魁梧的六爷,在我眼前显得更加伟岸,玉树临风般。我曾激动地将这些讲给我的同学听,言语中充满了自豪。打那以后,我就老爱问询关于六爷的事情。我姐姐曾给我说过,六爷第一次从外边回村,一袭中山装衣服,领回了一个漂亮的媳妇,高挑个儿,皮肤白皙,浓眉大眼的,高高的发髻挽在头上,穿一件翠绿色的花上衣,从街上走过,香脂四溢,惹得他们小孩子们好奇的围观,大人们也是投去惊艳羡慕的目光,这个媳妇便是六婆。从此,六爷就带着六婆扎根在村里。
六爷因病告老还乡后,并没有过享乐生活,兄弟姊妹们多,家庭生活贫寒,就连住房都成了问题,父母给他们分了一个一间半的偏厦房,吃住一体,到了雨季屋外下雨屋内漏,六婆用瓢盆在炕上接漏雨。狭小的房子,做饭时候烟熏火燎,特别在中午饭时,烟雾在屋内盘旋不出,熏得六婆老流泪,天长日久六婆患上了眼疾,见不得光照,见不得风吹,医生说那是“沙眼”。撂下杀敌的武器,捞起耕田的农具,六爷从此走上了农耕路,一辈子就和这土地打上了交道。八十年代,六爷在生产队任队长,村南头那个挂在电线杆子上的铜铃,就是六爷吆喝社员们下地干活的集结号,每当“当——当——当”的铃声响起时,这就是六爷在打铃,社员们便被召集在一起,六爷根据田间农活需求,安排每天每一晌的活路,田间管理,农活分配,一年的收成就掌管在六爷的指挥棒下。六爷管理严厉,作风过硬,社员们甚是敬畏,在那个大集体耕种土地的年代,总有个别人想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六爷要是知道了,那是绝对的毫不客气,而且总拿自己人开刀,所以人们就说六爷是“六亲不认”。六爷不那样认为,他不怕得罪亲友,他就是要一视同仁,只有那样,六爷管理才有底气,才能在社员跟前说硬气话!铁面无私的六爷也有他柔情的一面,每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解决人们吃粮紧缺问题,六爷曾多次步行到户县曲抱村他战友的村子,利用自己的关系好言为村民借粮,粮食借好后组织社员拉回村,帮助困难社员度过春荒。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六爷召集社员主持分田到户,从此,人们过上了不愁吃的日子,六爷也完成了他生产队队长的使命,自己带领一家人奋斗在自家的田间地头,过上了安稳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六爷料理家庭,始终秉承耕读传家的作风,她的五个子女中,有务农的,有上了大学在外上班的,六爷很是满足。
后来,我上了高中,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很少有时间回村里,对六爷的言行生活不甚了解,可是那个在杀场上奋勇杀敌英姿飒爽的形象,那个不屈不挠战斗的英雄气概永远在我的心目中,令我敬畏!
我家二哥,甚是感恩六爷,二哥说他的那条命是六爷给捡回的。1967年农历腊月,临近年关,那时的农村人都住土墙土房子,爱干净整洁的母亲,每到春节前就要用白土和泥水来涂抹灶台,寒假期间安排二哥和同伴们去河岸堎上挖白土,不料坍塌下来的大土块顺着土坡滚落下来,重重的压在二哥身上,被田地里干活的六爷发现了,六爷顺不顾身的奔过来,使尽全身力气刨开土块,背起奄奄一息的二哥直奔诊所,救下了二哥,脾气直率的六爷还重重的数落骂了我的母亲一顿。一家人感激不尽,等到二哥学业有成,每逢佳节回村里,就要去看望下六爷。2019年家里办了个书院,二哥回来,第一时间去看了六爷,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的艺术家们来书院写生,六爷是村里第一个被叫到书院当人物画模特的老汉,六爷上了年纪了,走路颤巍巍的,戴一副眼镜,一把旱烟袋不离手,挂在鼻梁上的眼镜低低的,像是要掉下来似的。一见到我二哥,笑眯眯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伸出布满褶皱的手,和我二哥俩紧紧地相握,两份不同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一份是无尽的感激,一份是赞许的喜悦。
六爷去了,带走了一个时代,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含辛茹苦,饱受风霜的六爷,踏遍了人生旅途的坎坷,圆满的走过了自己的一生,“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我不由得吟诵起李白的《行路难》,不知道是在感慨诗词的美好,还是在感慨六爷人生的不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六爷高寿,是上天的赏赐,是他那宽厚博大胸襟的折射!
六爷一路走好!
【作者简介】
田香蕊,陕西省周至县人,银行退休干部,文学爱好者,陕西省金融作协会员。
[编辑 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