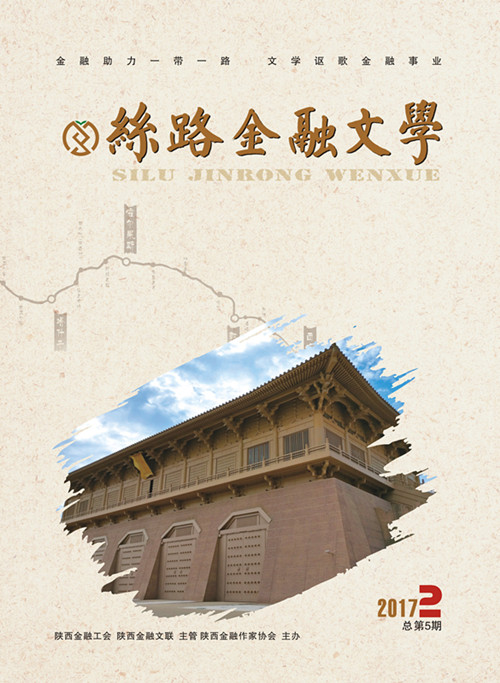实在没想到,我与冯琳热恋了两年多,就要挽臂步入婚姻殿堂之际,却突然发生变故而分手了。也更没想到,事件的起因竟然与扶贫的事儿有关。
我和冯琳是大学同班同学。因为都来自州城市辖内农村,彼此共同语言多些,平常遇到一起,总会操着家乡话聊聊天、说说笑。接触多了,彼此对对方就有了一个定性的看法。“你很像铁匠树,质硬,性倔,梗直。”她说。“那你就是翠雀花了。”我说,“纯朴,素雅,秀丽。”于是“铁匠树”和“翠雀花”就这样成为被彼此叫响并乐意接受的绰号。后来,也不知从那天起,我们又都经意不经意地喜欢并恋上对方了。最典型的细节是——每逢周末约见,我总少不了从校园那家小超市几乎不重样地买一把时尚小吃讨好她。而她呢,也总像小时候过年从大人那里得到几颗糖果一样,喜欢得什么似的,当着我的面吃得津津有味。然后她就掏出那把雕着梅花图案的指甲刀,特有耐心地给我修理手指甲,一修就是好半天。
天遂人意,毕业以后,她受聘于州城市国商银行,我被召为市政府公务员。于是我家就不失时机地将我俩唤了回去,按老家习俗,举行了颇为排场的订婚仪式。从此,每逢周末,铁匠树和翠雀花便会风雨无阻地移植于秀美的河滨公园。
河滨公园是州城的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十年前才在一毛不拔的丹江河滩上兴建起来的。放荡不羁而又乱石丛生的老河滩早就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南水北调丹江十里绕城长渠,渠边修筑了宽阔平坦的江滨大道,秀美的河滨公园,就宽宽窄窄地坐落于江滨大道和绕城长渠之间。园内林木葱郁,花香扑鼻,回廊亭阁,如画如诗。而且是一县一园,园园相连,各具特色,竞相媲美。如今这里已成为州城市民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当然,也更是恋人们周末约会游玩的一个惬意而固定的去处。
那天,也就是春节上班后的又一个周末在我的热切期盼中来临时,还没等我出门,心情就不由地像丹江激流一样格外激动起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有好消息告诉她。
我早早来到河滨公园门口,等了不一会儿,冯琳就满面春风地走了过来。我张开双臂迎上去紧紧一搂,然后与她手拉着手地步入公园。以往我们来这里,总是在游至尽兴或困乏之后,才去位于公园西段的岭南园歇下来。因为岭南园是冯琳的家乡岭南县出资修建的特色名园,并且集岭南名胜、文化于一身,她对岭南园情有独钟。但是现在,我们走马观花地游了不多一会儿,我就急切地拉着她走进岭南园的仿古凉亭,男左女右地在木质靠背条椅上坐下来。
我捧着她粉白玉润的脸庞热吻一阵后,依旧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另一只手将她白皙而柔软的小手握在手心,她便小鸟依人般地紧紧依偎在我的怀里。我和她都很享受这种氛围和感觉。
“喂,铁匠树,你今天好像很反常,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还没等我说话,直言快语的冯琳就欲揭晓我心里的秘密。
我笑了一下说:“那当然。人家有好消息告诉翠雀花嘛。”
她也笑一下说:“噢,那巧了,翠雀花也有好消息告诉你。”
“真的,那你先说。”
“还是你先说吧,感觉你的消息更激动人心。”
“那好吧,我先说。”我清了一下嗓门,我颁奖主持人似的隆重宣布:“历经数年携手跋涉,铁匠树和翠雀花喜结良缘的日子终于要到了,他老爸已择吉日,二月二龙抬头这天为这对恩爱恋人办喜事。”
我几乎是激动万分地说,没成想,冯琳脸色灿烂了那么一下,却旋即拨浪鼓似的摇着头说:“呀,不行啊。这事暂时不好考虑了。”
“为什么呀?你不是已经同意近期结婚么?”我直着眼睛问她。
春节期间,我和冯琳一起到双方老家拜年,两家双亲二老都欢喜不过地让尽快把婚事办了。并凑了首付款,让我俩在城里选了一处两室一厅婚房。之后,冯琳还满口答应,年后一上班就去扯结婚证的。这才过了几天,怎么就变卦了呢?难不成她是变心了?不情愿了?唉,真是人心隔肚皮,知面不知心啊!我心里不禁长出满腹的疑惑。
“我是同意近期结婚,”冯琳歉意地说,“可眼下情况有变,我马上要去定点扶贫村扶贫呢!刚才我说也有好消息告诉你,就是这事。”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绷紧的弦松弛下来,不以为然地说:“那不碍事,结婚归结婚,扶贫归扶贫,互不牵扯。挂钩帮扶,上班还在原单位,时不时地去检查检查、指导指导就完事了,没啥大不了的。”
“不是那样,”冯琳摇着头说,“这次要求挺严的,必须脱产离职,全程驻村。工作关系虽然还在原单位,但履职考核要拿扶贫实绩说话,并且一包三年,三年定点村必须全面实现脱贫目标。”
我思忖片刻,以退为守:“那咱去把结婚证一扯,回我家把事一过,然后你去扶你的贫,我不拦你。我爸把事都弄停当了,日子也定了,实在不好推辞呀。”
没想冯琳却依然固执地说:“不行的。任务这么重,是一场硬仗,压力山大啊!而且本周就得进驻。一进驻,工作千头万绪,哪有心思考虑这事。再说,那地方你也去过,偏僻、闭塞,交通不便,通讯落后,往后见面、联系都很不方便了。即便结了婚,成了家,也只能分居两地,天各一方地牵挂着,谁也照顾不了谁。何苦呢,还是再等等吧。你我都才不过二十四五岁,也别那么急嘛。”
唉!冯琳过去可不是这样,啥事都依着我的,这回咋就这么难商量。我垂头丧气地低下头。闷了许久,才又没好气地说:“你们银行也是,那么多男同志,谁去不行啊,非得指派你去,这是女娃子干的活吗?”
“不是指派,”冯琳解释道,“是我自愿报名要求去的。因为市国商银行担负的几个定点扶贫村,正好有我家乡岭南县寨东村,我在那土生土长,情况熟悉,乡亲们对我又很好,我早就巴望他们能够摆脱脱贫,富裕起来。再者,我娘家在那里,吃住问题好解决,于是我就试着报了名。”
竟然是她自己要求去的!我越发来了气:“你脑子进水了?好好的银行工作不干,怎么要求去干这烂事儿!”
“怎么说话的你?扶贫攻坚是国家战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你不懂。亏你还是公务员呢!”冯琳变脸失色地谴责。
我自知言辞不妥,遂缓和一下口气说:“就算我说的不对,那这么大的事,你事先怎不和我商量一下?”
“对不起,”冯琳抬手理着刘海,掩饰一下不悦的神色,说,“事情来得突然,来不及商量。头天,也就是前天才动员,然后自愿报名,组织审核,中间只隔一天,昨日就批下来了。再说,人家是有条件的,要素质高、有能力、有责任心和奉献精神才行,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所以我报了名实际也没抱啥希望,没想就被批准了,挺幸运的。”
冯琳这么一说,又像炮引子点燃了我的火气:“还幸运呢,分明是不幸嘛!好不容易走出山旮旯,上了大学,找到了好工作,现在又被发配回去当农民、服苦役,你还以为是好事,没有谁像你这么瓜的!”
冯琳受到刺激,脸一下憋得绯红,立即机关枪似的向我扫射:“服苦役就服苦役,只要能改变家乡面貌,换来乡亲幸福,那怕当一辈子农民,服一辈子苦役,我心甘,我情愿。你管不着,也无权干涉!”
初春的公园依然弥散着浓浓的寒冷。我的心也一下变得寒冷了。我转动着泪珠子的眼睛,盯着亭子外面冰冷的地面。地面上的一些枯叶被树林缝隙蹿过来的寒风来来回回地翻炒着。
“好好好,你高尚,你伟大。”我心里的火山终于喷发,“家庭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扶贫故,二者皆可抛。去实现你的扶贫梦去吧!我不管你,也不干涉你。”我胀红着脸,连讽刺带挖苦地撂下这么一些话,拧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气急败坏地回到出租屋,咕咚咕咚地灌了一肚子马尿,然后昏天黑地地睡了两天。第三天一大早,刚没精打采地起床,冯琳发来一条微信:
“我今天启程赴任了。都怪我不好,耽误了婚姻大事,让你失望了。但我既然接受了任务,就必须迎难而上,绝不动摇、退却。如果你有心等我你就等,我的怀抱永远是温热的;如果不想等,也不勉强,毕竟你有权重新选择。之于我,请放心,我会这般安慰自己:爱情是事业的动力,但如果失去了爱情,无牵无挂地去投身于事业,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再见。”
冯琳就是这样,凡事不苛求,一切顺其自然(这是我曾经对她的又一评价);我呢,比较任性,遇事不够冷静(这也是她曾经对我的又一评价)。失望、惆怅甚至怨恨还在心里泛滥着的我,对她的一意孤行实在忍无可忍,这一刻便将任性发挥到了极致,看完微信,我不仅没有回复只言片语,而且毫不犹豫地点了“删除”键。冯琳没有得到我的积极回应,也便关闭了心灵窗户,从此,就如不曾有过任何关系的陌路人一样,再也没有了任何音讯。
说来也巧,事过不久,扶贫的事儿偏偏让我也给摊上了。就在我与冯琳不欢而散之后没几天,单位安排我参加了一个扶贫干部培训班,然后我就被指派到一个叫石浪的贫困村扶贫去了。
说实话,接受了培训教育和领导谈话,我虽然基本理解了扶贫的确不是“烂事儿”,但任务接受的还是不那么痛快,因为听扶过贫的人说,驻村扶贫实实在在是一桩苦差事。果然,到石浪村实地一看,我的头就一下大了三圈。
石浪村位于秦岭南麓偏远山区,山大人稀,怪石嶙峋,远远望去,犹如波浪翻滚,故名石浪。散居于山窝窝里的几十户人家,就在那些石浪浪岩缝缝里将将就就地种着庄稼,连房子大的完整平地几乎都难找到几块。就是这个穷得连黄鼠狼都不肯尿尿的地方,之前曾被所在乡镇另眼看待,扶贫先拣好扶的扶,把资源匮乏,基础条件差,一时难以扶起的石浪村先撂在了一边。我去了也是束手无策,一丁点招都没有。只好厚着脸皮讨饭似的,这里拉点救助,那里弄点捐款,一年下来,村民们倒也时不时地得到了一些实惠,却无望从根儿上摆脱贫困。很显然,如此下去,三年脱贫目标必定泡汤。心里焦虑的我,整天就如针毡上睡觉,坐卧不
正在这个时候,我有幸参加了市上的一次扶贫工作会议。会上,岭南县扶贫办副主任梁晓忠在汇报本县扶贫工作情况时,突然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冯琳。我几乎是吓了一跳,以为听错了,赶紧扯长了耳朵仔细听。没错,就是表扬寨东驻村扶贫干部冯琳。说实话,一年的时空阻隔,我跟冯琳的恋爱关系虽然早已土崩瓦解,但思念和牵挂却时常在心里泛起波澜。尤其一直很渴望得到关于她的消息,却是连只言片语都不得而知。此刻从梁主任的口里才知,我们分手之后的一年里,冯琳的日子过得很艰辛,也很精彩,她用心血和智慧夯实了扶贫基础,也获得了岭南县“扶贫先进个人”和“优秀驻村干部”的傲人荣誉。真是金子放哪都闪光啊!我打心眼儿里为她高兴,却不禁鼻子一酸,眼眶潮湿了。
会后,我不失时机地循着梁主任的背影,走进他的宿舍拜访了他。
比较清廋的梁主任,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算是同龄人,一点不摆架子。见我也是会议代表,急忙起身与我握手,又忙不迭地让座、倒水。我自报家门之后,直奔话题:“听了您对扶贫干部冯琳的表扬,我深受感动,也很敬佩和惭愧,同为大学生扶贫干部,我与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还想从您这里再取点经,好好向她学习学习。”
“好的,关于冯琳的话题倒有的说。”梁主任欣然打开话匣子。
“起初,我在全县扶贫干部花名册里并没刻意关注到她。大约半年前,我下各点了解扶贫工作情况时,才知这位女大学生非同一般。过去我们县有些地方扶贫指导思想不端正,急功近利,热衷于搞面子工程,摆花架子,做假样子,花里胡哨地通过检查验收后,却很快又返贫。冯琳所在的寨东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她去以后,人们都摇着头说,‘碎碎个女娃能成啥精,还不是做做样子又走了,顶㞗用。’但冯琳不管旁人咋说,只顾忙着入户登记、摸底调查,然后郑重宣布:‘我保证,不出一年,就会找到生财的路子,所有外出务工人员都可回村在家门口挣钱;不出两年,农工贸效益和人均收入翻倍,脏乱差局面彻底改变;不出三年,实现全面脱贫,并初步达到文明、小康水平,有个新农村的样子。如这些目标落空,愧对父老乡亲,我冯琳绝不回城工作,这辈子也绝不嫁人。’”
“她的想法与众不同啊。”我打断梁主任的话说,“人都把村民赶出去务工,她却要将他们吸引回来就业;人都只盯着钱袋子指标,应付眼前,她却还考虑那么长远、那么全面,扶贫扶得有点宽了。”
“是的。目标明,愿景实,都是村民们所期待的。甚至不惜用青春和婚姻做赌注。所以群众一下有了信心,都愿意撸起袖子跟着干。”梁主任这般说着,话题却突然一转,“但是,她这么撂下‘大话’之后,人失踪了。”
“啊,失踪了?怎么会失踪呢?”我惊讶得喊叫起来。
“是的,失踪了。整整一个月都没见了人影儿。不过,就在人们议论纷纷、大失所望之际,她又出现了。”原来虚惊一场。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梁主任继续说:“当她又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几件大事办停当了:不仅从政府部门争取到一笔惠农资金,以个人信用担保办妥了一笔银行低息贷款,还出人意料地请回了3位在外打拼的企业人士回村投资、创业。时过不久,‘寨东建筑工程公司’、‘名优土特产种植基地’和‘绿色农特产品加工贸易公司’三大产业实体宣告成立。‘农民技能讲堂’也同时挂牌开讲,青壮年有青壮年的活,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事,人人进课堂,系统接受技能培训和素质教育后,就业上岗。这才不过一年,基础就很稳固了,局面也打开了。”
听到这里,我不禁赞叹:“一年之内办这么多实事大事,还不知她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心!”梁主任说:“这个可想而知。但是她本人从来不说,倒是村里韩老支书常常会唠叨她的一些事儿。我了解以后,梳理了一下,筛选出与钱有关系的几件事,写了一篇小通讯,叫做《驻村女干部冯琳扶贫二三事:借钱,骗钱,筹钱》。可惜她没让往外发,只在我县《扶贫工作通讯》上刊用了。”“有意思。讲给我听吧。”我颇有兴趣地说。梁主任便娓娓道来。
“年初,冯琳一进驻寨东,就理出两件当紧要办的事儿,一是改厕,二是改水。农家厕所我不说你也晓得,都是露天建在家门口、道路边,不文明也不卫生。尤其一到夏天,臭气熏天,蚊蝇肆虐。冯琳就把这事搁在心里,请来专家设计方案,准备统一改厕;村里饮用水也很不清洁,几条沟水上下共用不说,还洗饮不分、人畜同饮。冯琳采样去化验,果然污染严重超标。就请来技术人员一同爬山沟、钻密林,找到了几处合格山泉。但是,事想办,钱从哪来?两项工程除过村民义务出工外,也还需材料费、设备费18万元。这让她一时犯了难。村里付吧,眼下没有一分钱积累;让村民出吧,多数又拿不出这个钱。情急之下,她就将自己卡上、折上零零散散的钱倒腾到一起,然后又向单位预借一年工资,再又向单位几位同事借一些,总算凑够了数,这才保证了按期施工。时隔不久,全村家家就享有了无害化达标厕所,户户用上了方便卫生的自来水。直到年底,村里有了积累才给冯琳还了这笔账。”
梁主任说:“就在这次借钱垫款之后,冯琳又闹出一桩‘骗钱’的事儿。她在组织办实体的同时,动员全村特困户把家庭养殖种植也搞起来,可这些特困户几乎都拿不出资金引种育苗。为赶初春农时,冯琳想来想去,便悄然打起父亲的主意。因为她知道,身为民办公助教师的父亲,曾积攒了6万元辛苦钱,要留给她买家具家电作陪嫁。她对父亲说,爸,你把你给我攒的买嫁妆的钱先给我吧?父亲说你要结婚了,订嫁妆?女儿说结婚还早,我想作别的用。父亲说那不成,这个钱不能胡花,要专款专用,你啥时结婚我啥时给你。冯琳说我不胡花,我想拿去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利息高,增值快,很划算的。父亲这才信了女儿的话,就把钱给了女儿。没成想,冯琳将陪嫁款一‘骗’到手,就全部免息借给各家特困户应了急。直到年底,有了收获的特困户们给冯琳还钱,父亲才晓得了真相,抱怨道,‘你要借给他们你就直说嘛,咋要哄骗你爸?’女儿娇嗔地反问,‘我要直说了,你不情愿,我咋办?’”
梁主任说:“这第三件事就是‘筹钱’了。兴办实体是扶贫生财的好路子,但是路子好找,筹资却难。冯琳的办法是动员在外的生意人回乡投资。她上省城、下江南,愣是将寨东在外打工、创业的乡党一一走访了一遍,然后将目标投向了3名较有实力的成功人士。起初,他们都以为冯琳是来拉赞助的,就准备象征性地应付一下。冯琳说我不要一分赞助,我要请你们回村投资办实体。没成想,一位叫刘栋的建筑公司总经理却并不痛快,三番五次商谈之后,刘栋直言不讳地说,‘要我回去投资,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嫁给我。我这人事业有成,但婚姻不顺,奔四十的人了,还是单身。’冯琳咯咯咯地笑说,‘刘总你真会开玩笑。’刘栋说‘不是玩笑,是真心话。咱是同村人,你小时候我也见过多次,人排场、灵醒。现在成人了,更是貌美如花。我看中你了,只要你答应,我保证全力支持,不出一个月,我的分公司就会出现在寨东。’冯琳这才明白不是戏言,一脸红晕地笑了一阵,便将计就计,大方地说,‘好啊,只要你回村投资建实体,我就答应你。’但是,寨东工程建筑公司成立后,冯琳却变卦了,她将同期请回来投资的农贸公司总经理、三十出头的连晓聪女士介绍给刘栋,说,‘刘总,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大美女,你还是娶她为妻吧。’刘栋不禁一愣,笑说,‘冯琳你言而无信嘛,把我骗回来办了实体,却不想嫁我了。’冯琳真诚地说,‘连总人比我更漂亮、更优秀,而且事业有成,条件优越,你们更合适。’连晓聪咯咯地笑着捶打冯琳说,‘你乱点鸳鸯,我要撕了你的嘴!’心里却是喜欢。连晓聪也是寨东人,刘栋过去曾见过,这次同时回村筹办实体,也多有接触和了解,心里也就默认了。半年后,两人果然就双双踏上了红地毯。”
梁主任一气讲了三件事,后一件事听起来还很搞笑,我却没笑起来。我点点头,由衷地说:“她是动真情、下真功。把乡亲当亲人,把扶贫的事儿当自己的事了。”
“没错,”梁主任点着头肯定,“所以我说,冯琳扶贫的真经,其实就两个字:‘情’和‘真’。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学的东西。”
话说到这里,我们各自喝了几口茶,梁主任突然说:“我咋感觉你好像认识冯琳?”拿眼看着我。
我直言不讳地说:“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同学、是曾经的恋人。”
“我就说么,你的言语神情明显透露着某种暧昧的味道。”梁主任笑着说后,又抠起字眼:“那咋是‘曾经’?”
“分手了。”我苦笑了一下。
“为什么?”梁主任一脸诧异,“你俩看起还比较般配嘛。”
“为下乡扶贫么。”我说。然后就将我与冯琳分手的事件叙说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梁主任不无遗憾地说,“有没有希望和好?很好一个女娃,放手了可惜,如果你还爱她,我可以出面说和说和。”
“爱是爱的,但是不可能了。”我摇着头说,“已经冷战一年,彼此心都凉了。再说,同为扶贫干部,我的工作毫无起色,和她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了,哪有资格续缘。”
梁主任沉默片刻说:“听起来,你扶贫扶得不顺,说说,是啥情况?”
“唉,别提了,一塌糊涂。弄啥都难弄,弄啥啥不成。我现在退出的想法都有了,那怕丢了工作都行。”我唉声叹气地牢骚几句,就将石浪村的情况说与他,又打开手机让他看了看有关图片。
梁主任摇一下头说:“困难可以理解,退却、逃避我不赞成。那成龟子怂了(方言:意为没能耐,让人瞧不起)。”顿一下又说:“冯琳脑子灵活,你不妨向她请教一下,听听她的意见。”
我立刻拨浪鼓似的摇头:“不行,不行。我不想这个状况、这个时候与她联系。”
梁主任说:“那是这,我给她打电话试试,也许她有好主意。”就拨了冯琳电话。
“冯琳你好,我是梁晓忠。我在州城开会,你这边有什么事要办吗?”
“梁主任您好。谢谢,没什么事。前不久国商银行才派了人来慰问我,给予了诸多关怀,没啥后顾之忧,一切都好。”冯琳在电话那头说。
“那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方便吗?”
“没问题,你是我领导呀,只管吩咐。”
“那好。我有个老同学也在乡下扶贫,他那个村的情况也不是一般的差,扶贫难度很大,他现在工作很被动,想请你给把把脉,看如何是好。”梁主任接着就将石浪村的状况转述于冯琳。然后补充一句:“有几张图片,一会也发给你。”
这就成老同学了。我心里笑了一下。
“嗯,好的,我想想,就怕想不出来,交不了卷哟。”冯琳谦虚道。
“没事,我相信你。不过也不急,你先考虑下,过一向我去寨东当面听你意见。”梁主任挂了电话,与我交换了电话号码。之后说:“等我回电话。”我不无感激地说声谢谢,起身告辞。
“有话捎给她吗?我很快就去寨东。”梁主任起身送至门口说。
我犹豫片刻说:“不必了。在她面前不要提起我。方便的话,请代我关心点她就行了。”
“明白。”梁主任点一下头,似乎话中有话地说,“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责任编辑 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