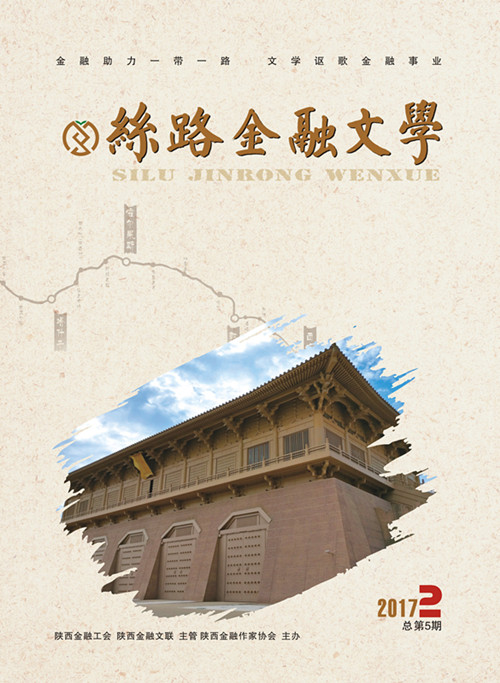永远的博格达
作者:薛云利
题记:柔韧漂亮的丝绸牵起长安与新疆民族团结的手
一
在天山南北的辽阔土地上,驻扎着一支战时扛枪卫国,平时种田务农的特殊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来自祖国的首都北京,富饶的秦川大地,美丽的南国小镇……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安家在塔里木河边,做一名毛主席的军垦战士,为伟大祖国把青春贡献。他们象红柳扎根在戈壁,战胜风沙开拓万顷荒原。接过先辈在南泥湾的镢头,艰苦奋斗的精神代代相传……
朱邦胜就是为了这个革命目标走进了新疆。
1965年,24岁的朱邦胜从陕西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后,毫不犹豫地在毕业去向表上写下了“支边赴疆”四个字。他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坐了8天8夜的火车才到了乌鲁木齐市。在农垦厅报到后。人事局的一位老同志笑眯眯地说:“小伙子,本来我们要把你留在厅里的,可建设兵团的六运湖农场听说分来一个农机师,非要不可,他们急等着你去维修机械化连‘趴窝’的好几台‘东方红’,接你的车在楼下都等两天了。”一听这话,一种被需要、被信任的感觉让朱邦胜激情澎湃。“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现在就去报到!”说着把撂在地上的行李一背,下楼了。可楼下哪有什么汽车,一辆半新不旧的手扶拖拉机停在墙角,一个浓眉大眼的维族小青年正斜靠在车厢旁打瞌睡,朱邦胜把行李往车厢一撂,还把小青年给吓了一跳。
“嗨呀!阿里木,我们可终于把你盼来了!”小青年握住朱邦胜的手激动地说。随即他又跳上车厢,麻利地把朱邦胜的铺盖卷打开,“路还远着呢,我开慢点,你好好睡一觉就到了。”维族小青年的热情,让从未和少数民族打过交道的朱邦胜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拖拉机冒着黑烟开始在崎岖不平的“搓板路”上欢快地跑了起来。尽管坐在车厢上七摇八晃的,但连续坐了好多天火车朱邦胜还是很快就睡着了。夜色已深,凉风习习,行驶了数百公里后,这位可爱的维族小青年,时常将拖拉机停下来,帮朱邦胜掖好被子。
“阿里木,阿里木!”睡得正香的朱邦胜听到有人在叫他。“到了,六运湖欢迎你,快下车吧!”
“哈德尔,阿里木今晚就先住你们家。”
“好冽。”
夜黑沉沉的,朱邦胜正想揉揉眼睛看看这地方是啥模样,就被机械化连的维族老农工哈德尔热情地拉进了地窝子。哈德尔是最早进六运湖农场的工人,说话不多,憨厚忠诚,待人格外热心。
第二天一大早,朱邦胜悄悄地从地窝子爬了出来,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将要奉献青春和热血的这块地方。
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盐碱地,没有绿色,没有楼房,没有马路,没有电线杆,近处的几块高地上,零星地散落着几间东倒西歪的茅草屋,更多的家都隐藏在地平线下的“地窝子”。远处的博格达冰峰象一个威严的武士,剑刺天际,傲立苍穹。
“无限风光在险峰”。朱邦胜忽然想起了毛主席语录里的这句话。
他知道眼前这一个个潮湿的地窝子里,住的全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他们喝着盐碱水,啃着窝窝头,辛勤地在这片热土上劳作着。为了边疆的繁荣,为了让土地荒漠的新疆披上绿装,他们把满腔热血与青春年华都奉献在了这里。
站在亘古荒原上,朱邦胜思想起了妻子林小燕和两个可爱的孩子。这会儿,她们在家里干什么呢?小燕一定起来了,孩子们肯定还在被窝里睡懒觉。
朱邦胜脸上浮起了微笑。把家搬过来,把根留在这里,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下定了决心。
朱邦胜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工作。白天,他在农场的田地里来回跑,观察各类机器的运转情况,给驾驶员讲解维护和保养机电的注意事项。晚上,他把连队所有的机器都要逐个检查一遍,把嵌进轮胎里的稻草拔出来,给劳累了一天的“东方红”喝点机油。有时为了确保第二天机器照常运转,他一干就是几个通宵。
二
春天红柳吐绿的时候,林小燕要来新疆了。为了让一家几口住得更宽敞些,朱邦胜重新选择了一块比较干燥的平地。哈德尔和老伴阿衣良孜主动过来帮忙。由于土质比较硬,朱邦胜没挖几下就累得气喘喘吁吁,哈德尔一乐说:“修理机器你是行家,干这活你还要看我的!”他熟练地用镢头挖着,很快一个四方的坑就初见雏形,一旁的阿衣良孜给他们又倒开水,又递毛巾,忙得不亦乐乎。坑挖好了,可是没有封顶的木头。哈德尔就从家里搬来准备钉家具用的两块木板,破成了木条,固定在顶上。朱邦胜看到,在搬木板的时候,哈德尔夫妇没有任何迟疑,这两块木板要花掉哈德尔夫妇多少积蓄啊,可他们毫不犹豫的送给了自己,这使朱邦胜受到强烈的震撼。
按照政策,林小燕被招工进农场当了一名农工。和这么多少数民族职工和干部在一起,自己能处得来吗?林小燕的心里犯开了嘀咕。尽管语言不通,习惯不同,但一个手势,一个真诚的微笑,一个小小的帮助,都让她感到被理解和沟通的幸福。善良的哈德尔夫妇,热情的哈族姑娘哈比巴,从他们的身上,林小燕感觉到了亲情般的温暖,她爱上了这片土地,爱上了这里的人们!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农垦战士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把一个不毛之地的六运湖农场改变成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小江南。一片片水稻翻滚着金色的浪花,一块块棉花地象成群的绵羊散落在辽阔的原野上。机械化连的所有员工,家家户户都从地窝子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新盖的茅草屋。
哈比巴美丽动人,性格开朗。金秋10月,她生下一个女孩,她的丈夫那扎尔拜克兴奋的不得了,给女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古丽健,意思是美丽的花朵。像是无言的约定,那家的喜讯刚刚传来,朱家又添人丁。同年11月份,朱邦胜的三女儿朱学慧也出生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宝宝,象联系感情的纽带,把两家的关系拉得更近了。他们对待两个小孩从来不分你我,有时哈比巴外出,古丽健就吃林妈妈的奶,哪家出去给小孩买东西,都是两份。他们说:“小孩吃百家饭长大好养!”至今,古丽健和朱学慧长得就像一对孪生姐妹。
“小燕,能让我的孩子叫你妈妈吗?我和那扎尔拜克商量过了,你能答应吗?”一天,哈比巴用一双诚恳的大眼睛征求林小燕的意见。按照风俗习惯和礼教,把自己的孩子认汉族人作父母,通常是没有的,这对朱邦胜一家来说,无疑一种特别的信任和尊重。
“我同意!亲爱的哈比巴,我的孩子也叫你妈妈,咱们就是干亲了。”林小燕愉快地答应了哈比巴。
农历11月,新疆已是冰天雪地,一片茫茫银海。当时农场宁愿让自己饿肚子也要尽量把更多的粮食上交给国家。在只有高梁、玉米添肚子的年代,林小燕的月子坐的很清苦。由于连小米汤都喝不上,她的身子十分虚弱。农场里的菜实行定量供应,分的一点土豆,一家人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细心的哈比巴观察到了这一切,并告诉了丈夫。
“你放心,我就是翻过天山去,也要给老朱家找来小米!”那扎尔拜克骑上他那匹高头大马,鞭子一甩,马蹄子踢起的积雪四溅,很快就被消失在银白色的世界里。
新疆并不产谷子,要买点小米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扎尔拜克骑着马走遍了阜康城的大街小巷也没有买到,但他并不罢休,又策马跑到自己的家乡阿勒泰附近。整整打问了一天一夜,终于在一个哈族牧民家里,为老朱驮回来了20斤金灿灿的小米。
望着脸被冻得发紫的那扎尔拜克,朱邦胜和林小燕的眼里盈满了泪水。要知道,哈比巴此时同样需要“营养品”,可那扎尔拜克把买来的小米全部给了他们。
后来,那扎尔拜克又从熟悉的牧民手里为朱邦胜买回来几袋土豆。这并不起眼的土豆,保证了朱邦胜一家五口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农历春分,在哈族人隆重庆祝肉孜节的时候,朱邦胜郑重地让女儿朱学慧认哈比巴作了干妈,并给女儿取了一个哈族名字,跟了那扎尔拜克的姓,叫那新。
农场没有幼儿园,为了更好地工作,1971年的春天,林小燕和哈比巴把刚满1岁的那新和古丽健一起托付给啥德尔的老伴阿衣良孜看护。刚刚跚跚学步的古丽健和那新十分调皮,常常把屋子弄得一团糟,两个孩子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一会儿要拉屎拉尿,善良的维族老妈妈,待她们比自己的亲生女儿还要亲,没有让这两个孩子摔过一个跟头,擦破一点皮。在当时食品紧张,一小块黑面饼都要掰成四块,过年的一小块糖都要敲碎分着吃的情况下,她把家里最好吃的酸奶疙瘩拿出来给孩子们吃。一把屎一把尿,把这两个孩子看管到三岁。林小燕和哈比巴想送给阿衣良孜点钱物,都被她一一拒绝,这位不善言语的老妈妈说了一句话:“只要你们能安心工作,我就满足了!”
动乱年代,那扎尔拜克受到迫害,亲戚朋友都与他划清界限,惟有朱邦胜给他送来了日用品和食品,并安慰、鼓励他直面人生的信心。
真挚深厚的情谊没有民族界限。在太阳冲出云层的日子里,那扎尔拜克感慨地说:“我头上扣着那么高的帽子,脖子上挂着这么大的牌子,连亲人都不敢理我,可老朱不怕,他看望我、安慰我,这是什么,这是永恒、纯洁的博格达冰峰。”
三
六运湖农场朱邦胜的窑洞里。那扎尔拜克、哈比巴,哈德尔、阿依良孜,还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静静地坐在坑上,正中的桌子上,摆放着早已放凉了的酒菜。没有人说话,每个人的眼睛里噙满了伤感的泪水。
朱邦胜要调回陕西老家去。三封加急电报写着同一行字:父母病危,无人照料。如果说简单地回家探亲那倒没有什么,可是要举家离开自己生活、工作、奋斗了近20年的地方,朱邦胜和林小燕的心里很难受,作为拓荒者,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他们的情和爱。舍不得啊,热情、豪爽的那扎尔拜克,知书达理的哈比巴,诚实的哈德尔,善良的老妈妈何依良孜,这一别,何日能够相见?
朱邦胜让自己的孩子们跪下,给维族、哈族的亲人们磕了三个响头。他流着眼泪说:“孩子们,你们是喝着酸奶、吃着羊肉长大的,无论将来在哪里,始终要记住,他们是我们朱家最亲的亲人!”朱邦胜清楚地知道,在这举目无亲的大漠边疆,在这艰难创业的日日夜夜里,如果没有维、哈亲人的帮助,自己无论如何是拉扯不大四个孩子的。
12岁的那新抚摸着阿衣良孜布满沟壑的双手流着泪说:“奶奶,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说着,又扑到哈比巴的怀里,哽咽着说:“妈妈,你会想我吗?”孩子的话,让阿衣良孜、哈比巴、林小燕泪如雨下。古丽健拿着小手绢,不住地给自己的汉族妈妈林小燕擦着眼泪。
“是神灵博格达峰赐给我们的友谊。老朱, 别忘了,新疆是你的家,你一定要回来的!”那扎尔拜克难受地说不下去了。哈德尔含着热泪,默默地帮他们捆绑一堆要带走的东西。
别了,六运湖;别了,博格达峰;别了,我的少数民族父老兄妹。
火车启动了,朱邦胜倚在座椅的靠背上,任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
20年,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20年。
离开新疆的时候,那扎尔拜克曾把自己今后的打算告诉给朱邦胜。他想带着哈比巴回到自己的家乡阿勒泰放牧去,家乡父老特别需要他这个兽医。等朱邦胜的工作稳定后,林小燕曾给哈比巴写了几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沓无音信。于是他们想,那扎尔拜克一定是搬到阿勒泰去了,也许那一次分别真的就是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
20年中,每一个哈族和维族的“开斋节”、“肉孜节”,林小燕都要做一顿香喷喷的羊肉抓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怀念着新疆的日子,朱邦胜总会摇摇头说:“这饭没有哈比巴做的香,这油茶没有阿衣良孜家的好。”有人说时间能够淡忘一切,但对于朱邦胜夫妇来说,这种深厚的民族情谊是一生永远忘不掉的。四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在父母的感染下,新疆生活的每一个片段都如一段汩汩流淌的清泉,始终在他们的心里弹奏着甜美的歌谣。神奇的博格达峰,宽阔的草原,香甜的酸奶疙瘩,都是他们童年生活最美好的回忆。特别是二女儿朱学梅的印象更为深刻,那个年代,正好是她金子般的少女时期,直到现在,不论走到哪里,她都自豪地说,“我是喝着天山雪水长大的,我是新疆人!”
朱学梅结婚后,将这个凝聚着浓浓民族深情的故事告诉了丈夫杨康虎。身为军人的杨康虎被被故事里的人物深深地打动了,他答应妻子一定要找到新疆的维、哈亲人。10多年的时间里,他曾三次利用去新疆出差的机会,抽空打听六运湖农场,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朱邦胜和林小燕已是年迈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说,找到当年的亲人,就等于找回了整个年青时代。面对双亲,朱学梅夫妇感到十分愧疚。
远在新疆的哈比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朱家。由于只知道老朱调回了陕西,具体什么单位还不清楚。他们曾专门回到六运湖农场,找到农场采购武纪元打探消息,但在当时一无电话,二无详细地址的情况下,他们逐渐失去了寻找的信心。但哈比巴不甘心,女儿古丽健在上海进修医师的时候,她专门让古丽健绕道西安,试着寻找她的汉族爸爸和妈妈,但次次都让她失望……
这一切,似乎只能成为一段回忆和值得人品味的故事。这一切,似乎只能是永远的思念和绵长久远的呼唤!
四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
在西安开往乌市的火车上,躺在卧铺上的朱学梅显得无比兴奋。几回回梦里回新疆,这次真的就要实现了。在新疆开会的丈夫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给妻子圆梦,便特意打电话,让她乘火车速来新疆。
去六运湖,去找那扎尔拜克,去看看善良的阿衣良孜,去寻回儿时的记忆………
到了,到了,当司机说六运湖到了的时候,朱学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哪里还有六运湖的影子?
一排排整齐的楼房鳞次栉比,一辆辆崭新的汽车、收割机、播种机整齐的排列着,宽阔的水泥路通向了田野深处,田地里铺天盖地的棉花正翻滚着洁白的浪花,看不见茅草屋,找不到破毡房,踩不着盐碱地,一个肥沃的绿洲,一个现代化农场展现在他们面前。农场的马路上,年轻的小伙子们骑着崭新的摩托车来来往往,美丽的姑娘坐在轻巧的木兰摩托上徐徐而行。
“我走过许多地方,最美还是我们新疆……”耳畔飘来的歌声让他们的眼前为之一亮。
“变了,一切都变了,没有当年的一点影子!”站在自己当年上学的农场小学的楼房旁边,朱学梅感慨万千。这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一边打量一边问:“同志,你们找谁?”
“你是,武纪元大叔?”朱学梅惊喜地喊道。
“你是朱邦胜的二女子,朱学梅!”老人也一眼认出了朱学梅。
20多年了恍若隔世,这一老一少却在瞬间认出了对方。但那个年代的事和人,纵然沧海桑田,都在这一刻清晰而亲切地印现在眼前。
在武大叔家的独门小院里,他们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交谈中老人说,阿衣良孜已经去世,那扎尔拜克和哈比巴还应该住在阜康,也许还在兽医站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朱学梅心情特别复杂,既为知道那扎尔拜克的情况而高兴,又为阿衣良孜的离去而悲痛。“去阜康市,现在就走!”他们谢绝了老人的热情挽留,立即乘车直奔阜康。
车到阜康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昔日的阜康已撤县设市,宽敞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七彩的霓虹灯光把这个边塞小城打扮的像一位时尚的少女。穿着民族盛装的维吾尔族、哈族青年,在大街上悠闲地散步,凉爽的微风把烤羊肉串的香味吹进人的鼻子里。
以前的兽医站早已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卖牲畜用药的药店。
“您知道这里有个叫那扎尔拜克的人吗?”朱学梅向卖药的姑娘打听,见姑娘疑惑便解释说:“老早以前,他在这兽医站工作。”
“这很像一个市领导的名字,你们去市政府打听一下吧。”姑娘想了想说。
“那扎尔拜克当了市领导?”朱学梅有点迟疑。“20多年了,从六运湖农场的变化你就可以知道,没有什么不可能,赶快走吧!”丈夫催促着。
机关已经下班了。值班的维族小伙子认真地询问了他们的身份后,说:“政协有个老主席叫那扎尔拜克,不妨去政协问一问。”
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小伙了忽然一拍脑门说:“对了,今天有个哈族人结婚,这会儿正在旁边的大酒店办宴席呢,城里所有的哈族人都在,那主席肯定也在。”这使他们喜出望外。
果然,离政府大楼不远的一家酒店里,一群群哈族人不断地出出进进。杨康虎正要迈脚往进走的时候,被朱学梅一把拉住。哈族人结婚是有讲究的,佰生的汉人闯进去,坏了人家的规矩可不得了。他们拦住了一个哈族小伙子,说明来意后,小年青高兴地说:“你们找对人了,我就是那扎尔拜克老伴哈比巴的侄子!”听了这话,他们为连日来的奔波有了收获而格外激动。
哈族青年领着他们来到市政协家属院。在一大片绿荫荫的葡萄架下,那扎尔拜克正和几个老干部一块儿下棋。
“你是那扎尔拜克爸爸吗?”激动的朱学梅声音颤抖地说。
“你是?”那扎尔拜克揉了揉眼睛,怎么也想不到军车上下来的这位汉族女士叫自己爸爸。
“朱邦胜,六运湖,那新,我是朱学梅!”
“朱邦胜,你是老朱的女儿!”那扎尔拜克紧紧地握住了汉族女儿的手。
“慢点,姑父,你不要激动!”他的侄子赶紧扶住了因激动两手发抖的那扎尔拜克。
“我以为这一生再也不会有老朱的消息了,没想到啊,没想到……”那扎尔拜克老泪纵横地说。“快打电话,把你哈比巴姑妈,把所有的亲友全给我叫回来!”他吩咐侄子。
“好女儿,我们一块在隔壁的哈族大酒店吃饭,爸爸妈妈有太多的话要问你!”
“我们已经吃过饭了!”朱学梅说。
“不行,一定要吃!”说着,那扎尔拜克拉着他们一起来到了酒店。
哈比巴来了,她搂着朱学梅泪如雨下,“是天山的风把我的女儿给吹来了,感谢神灵博格达峰!”满头银发的哈比巴不住地念叨着。古丽健不住地给朱学梅夹着菜:“爸爸妈妈好吗,哥哥和妹妹他们过得都好吗?”
这一大家子哈族人和几个汉人的的喧闹,以及他们喜极而泣的神情引来了酒店许多客人好奇的目光。一位哈族老人说:“那主席,你怎么有一个汉族女儿?”“不是有一个,而是有好几个!”那扎尔拜克兴奋地说。当他把这段故事讲完后,饭店里所有的人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客人说,“想不到,想不到!我们哈族那主席竟然有这样一个生死之交的汉族兄弟,哈、汉一家人啊!”
席间,他们拔通了远在西安的朱邦胜的电话,中断了20多年的友情重新续燃……
电话里,经历了世纪沧桑的4位老人共同许下一个美好的约定:羊年,博格达峰脚下,再相会……
作者简介:薛云利,笔名:大河奔流。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现任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监察部纪委办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