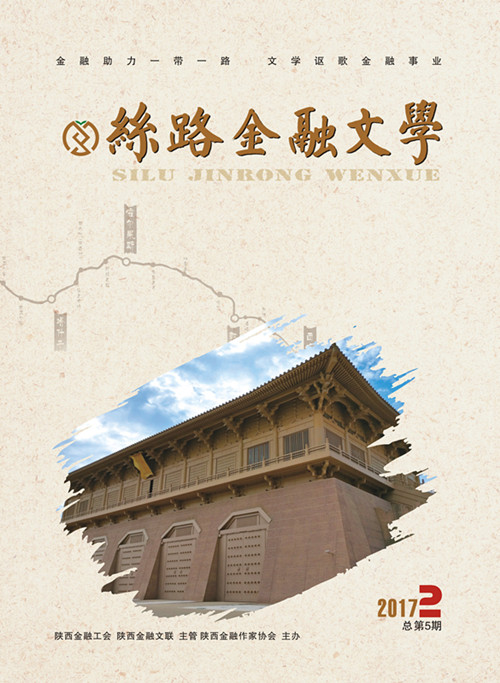十岁那年,城乡路上有矮平房,有水石桥,还有南廊棚。
我每天从南面走到北面,就像在一幅铅笔画里,无需改变颜色。路上的行人都是熟悉的面孔,他们热络叫着我的小名,我对他们报以恭敬微笑。当然,这些人的个子要比我高很多,我看着他们的时候是仰视,明亮的阳光从浓密的树荫落下,金芒乍现。
父亲说,太亮的光线对眼睛不好。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为我的视力担忧,这可能与他的散光眼镜有关。虽然,这幅黑框眼镜多数时间被他收在镜盒中,但据说散光会遗传,遗传两个字,带着强大的不可抗力,临字帖的时候我老是写不好。但凡不上学的日子,父亲极力主张我去弄堂里逛逛,找街坊的小伙伴玩。
我家住的弄堂一共才三户人家,是整条城乡路上最小的弄堂。入口处第一家住户门庭最大,占了整个弄堂的二分之一。这家男主人整天肃了一张脸,眉头像把拧紧的锁,每回看到他我心里总发毛,想着今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他家有个比我大十岁的儿子,据说在外省市读书,一年难得看见几次。这家人姓张,这个姓氏不好写,字带棱角,剑走偏锋。我还是喜欢我家对面的人家,他家姓陆,屋子和我家一般大,一间平房外带一间自搭的灶片间。夫妻俩都在镇上的公交站上班,家中的儿子虎头虎脑,刚刚念幼儿园,平日里由奶奶领着,住在乡下。
我成了我家弄堂里唯一的小孩,习惯了一个人在葡萄架下泡中萃牌方便面,我在吃里寻找着乐趣,这种与食物相交的喜好,经年后未曾改变。那时父亲在交通局附属的船厂上班,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六点后回家。他带我去他的单位,只一次,我终生难忘。那日,天晴日暖,整齐的四层楼,一排排的办公室,墙壁白得能反光。父亲牵着我,一面走一面微笑,与迎面遇到的同事温和招呼。每一个人都很高兴,见到他仿佛见到了暖融的阳光。走廊的尽头有高高的廊柱,一只灰黑色的燕巢筑在水泥檐下。我欢呼雀跃,看见燕巢了,出现在课本里的燕巢竟在我眼前了。探出脑袋的小燕子,用黑亮的眼睛打量着我,发出清脆地鸣叫,我们彼此交换着眼神,传递童年的暗语。我看向平日不苟言笑的父亲,感激地想下辈子依然要做您的女儿。
这个心愿在父亲带我去隔壁弄堂古家后变得更加坚定。古字天高地远,自带一股清香气。古家有四个女儿,我如遇火星般盯着眼前的屋子,虽然南边有一排木窗,但屋子的空间太大了,日光竟然照不到我们坐着的桌前。父亲和古伯伯熟络地寒暄,聊着送教代课的事。过来的路上父亲告诉我,这位古伯伯年纪比他大好多岁,在镇上文化馆创作组工作。创作是什么概念,我不懂,我只关心他家的小女儿长什么样子,因为父亲告诉我她与我同年出生,她的名字叫玉琴。
我终于有自己的玩伴了,可以每天做完功课后在水泥台上打乒乓,在弄堂里跳橡皮筋,而且是在离家只有一百米远的地方。玉琴很瘦,眼睛细细的,辫子细细的,说话的声音倒是非常响亮干脆。确切的说,他们一家人都这样,他们高兴的时候笑声会在房梁上打转。房梁是木质的,架空着屋顶。一只透明的灯泡垂在落下的电线上,只要抬头,就可以看见。这是整间屋子里唯一的灯具。抬头的时候还可以看见挂在房梁上的竹篮子,三三两两,玉琴每回指着篮子,促狭地对我挤起眼睛,我就知道里面有她隆重推荐的落苏干(紫茄子晒干后腌制)、黄瓜干和饭糍。
我好生羡慕玉琴,家里不光屋子大,而且屋子后面还有个宽敞的院子。院子打着密密的篱笆,玉琴的母亲用大黑卡子牢牢夹住两鬓的白发,每日早上弯着腰在里面打理蔬菜。如果黄昏的候我去找玉琴,她多半端着个蓝花瓷碗,倚在家门口的门柱上。一边嚼着落苏干,一边吃着茶道饭(用开水浸泡的饭糍),她说这是人间的美味。重要的是还有夕阳可以看。真的,顺着她的目光看去,绚丽的晚霞好像是天空打翻的水彩颜料,四处流溢。琉璃金、玫瑰粉、紫柑橙,晕染交错,红红的落日在其间温柔隐退。我陪着她一起看,一起嚼着落苏干,惬意极了。玉琴说得没错,这是人间的美味。
我从没有见过玉琴的大姐,但她却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玉琴说大姐脾气最好,从来不对她凶,可惜,大姐要长她十多岁,在她八岁时就嫁到外镇去了。我见过玉琴的二姐,皮肤白得像冬天的雪,架着一副眼镜,很少说话,整日捧着本书。玉琴很怕她,我觉得她特别像我的语文老师,果然,她后来考上了师范,做了小学语文老师。玉琴的三姐像极了《小妇人》动画片里的简,她比玉琴还瘦,却是学校的长跑冠军,我知道每次玉琴主动来我家找我玩的时候,一定是她三姐和玉琴妈又在家里论理,我能想象到她极具穿透力的声音正挑战着屋顶和四壁。后来,她也做了老师,教体育,据说还是教研组长。
至于玉琴长大后做了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小学毕业那年,我离开了城乡路,并且再也没有回去。我看着自己似若珍宝的洋娃娃被放进新公房的装饰橱,父亲抚摸着我的脑袋,向我介绍阳台对面的学校。我是中学生了,一个剪着游泳头的女中学生,我会骑二十四寸的自行车,除了成绩好,没有什么特长。搬进新公房后不久,父亲的单位解散了,原本寡言的父亲更沉默了,他在家里画镜面图,刻广告字,后来直接去了镇上的工人俱乐部画墙面广告。
二室一厅的新公房空落落的,我爱上了放学后在校园里游晃。那年,我十四岁,身高一米六十三,体重八十四斤。体育课称体重时,副班长笑着说,“You much little!”副班长个子比我还高,她很会说话,也会笼络人,同学们都围着她转,我这个班长倒成了多余。班级改选那天,我正好去市里参加作文比赛。我对职务没什么兴趣,这种呈现好像命里带来的,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我的一生有多长,我并不知道。很多年以后,一名女政客对我提到“做领导只上不下”时,我一笑了之。
偶尔,我也会下象棋,因为学校的象棋比赛每班必须要有人参加。我一度怀疑自己的水平,结果跌跌撞撞一路进入复赛。我和年级里其他班级的男生对弈,观看的学生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我面似大义凛然,摆出一幅气吞山河的架势,实则手心捏汗,脚底直冒冷气。如果父亲在就好了,平时和他对弈,他总是先拿掉三子,车、马、炮,我的“将”还是败在他的手下。我的头发已从游泳头长到了齐肩发,我继承了他的容貌却没有继承他的智商。
棋是输定了,不过也有意外,隔壁班的女生主动找我搭讪。她叫洁,与我同名。她身材窈窕,气质极好,天生一副衣服架子。眼睛也是细细的,不过一管鼻子又挺又直,我笑着说她像吴倩莲,她也笑,她说我像方季惟。我们约了一起逛展销会,一年一度的展销会是镇上的头等大事,本县的外县的商家都会出来摆摊,场面比过年还热闹。我们一起去看最新式的羊毛衫还有电子表,洁出手很阔绰,看到喜欢的就买。我一路跟着她,像大户人家的贴身丫鬟,有时,我会站在卖贴纸的摊位前踌躇一下,洁看到了,毫不犹豫买下我眼前的贴纸,回头说道,“拿着,等会我带你去吃小馄饨。”
对于吃,我从来都不会抗拒。我一边舀着小馄饨一边听洁说她的父亲。洁的父亲是镇上五金电器公司经理,用时髦的说法她是富二代。可她的父亲不和她住在一起,她和母亲住,她每月去父亲那里拿钱,她不喜欢她父亲,更讨厌父亲那边的女人,她称她为狐狸精。我撇撇嘴,忽然觉得刚刚送到嘴里的馄饨有点烫,烫得我鼻子发酸。我没有告诉洁,我和父亲住,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自那以后,洁经常来我家楼下找我,有时是周末,有时是假日。日子不咸不淡,学业不紧不慢。每次出门,父亲会叮嘱我早点回家。夏天到来时,父亲一再强调出去玩要穿长裤,这个要求无形促成了我特有的着装习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穿裙装。
我和洁成了同学眼中同出同进的好友,至于有多好,我说不上来,我只知道她不开心的时候一定会来找我,我们一起去工人俱乐部的录像厅看电影,她喜欢刘德华我喜欢郑少秋。她会买成盒成盒的录音带,从小虎队到四大天王,无论正版的还是盗版的。和洁出去晃悠的时间多了,看书的时间自然少了,成绩变得越来越难看,从前列到了倒数。
班主任很是着急,上门来家访。一个劲强调初三下学期的紧迫性,父亲抱歉地赔着不是,日光灯照着他额头上的皱纹,一刀一刀刻进我心里。我站在旁边,眼里噙着泪水,大气不敢出。第二天,我背上书包,出门前向父亲郑重保证,一定好好学习。我主动去洁的班级找她,和她打招呼,中考前先不出去玩,等考完了再约。洁失望地嗯了一声,转身离去。君子重承诺,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气度,但仅仅是我有。中考放榜后,我考上了市区的银行职校,洁去了乡里的技术学校。等我再找到她的时候,我戴着新配的眼镜,她烫了波浪的卷发,口红涂得猩红,在一个中年男人怀里嗔笑,看见我露出冰山一般的冷漠。我的心底一片荒凉,传出鲜花凋零的声音。我走在夏夜漆黑的风中,感到彻骨的冬寒。我取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眼前的世界被泪水打得一片模糊。
进了银校,我依然当班长。开学时站在讲台前做班级点名,我把一名市区女同学“王岚”读成了“王风”,那名女同学愤然起身,投来鄙夷的眼神,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我暗暗发誓努力读书,不再犯错。此后日日勤奋,拿了三年的奖学金,同学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拼命三娘”。银校前面有条马路叫水电路,听说周边的居民小区三天两头停水断电。学校将废弃的幼儿园略做改建,成了郊县生的寝室,二十人一间。别的同学熄灯后小声谈话,谈论着学校、谈论着老师、谈论着市区同学。我因为记得开学初的窘态,处处小心翼翼,把自己埋进被子,一言不发。
一种状态习惯久了也会溶入性格。银校毕业后我去镇里银行报道,干练的女行长一见我就说这个姑娘谨小慎微,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喘。还好,当时学校包分配。干了几年银行柜面,行里竟安排不善辞令的我去了市场发展部。拿到调令那天,我啼笑皆非,每天奔东走西,每天和不同的人握手交谈,生活一惊一乍,场面波澜壮阔。那时我的车很小,总爱往海边跑。海湾离居住的小镇不远,走高速公路只需三十分钟光景。双休日我会带上白色的笔记本电脑,去那里坐上一天,记录一周的行程,和行程里遇见的人或事。渐渐的,我的文字被镇上小报刊登了,这令我有点吃惊。
再后来,有一位带帽子的老人来找我说出书的事,我茫然地望着他,不知所措。他不光找了我,还找了一位叫伽的女子。我第一次见到伽,是在老人的办公室里,伽说她比我大五岁,我称她为姐。由于一起出书,伽经常打我电话,一会聊书号的事、一会聊文章的事,聊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老人,我告诉她,我和老人只是一面之交。
伽似乎人缘很广,每天都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她忙碌地打着我的电话,三天一回,两天一次,我安静地听完,挂上电话,低头忙碌手上的工作。删繁就简,是我一贯的生活态度,至始至终。历时半年,书出版了。伽又来电话,说她的领导要看我的书。我心中纳闷,她的领导我仅见过两次,纯属工作拜访,但电话那头伽言辞恳切,出于礼貌,我答应了。她火急火燎乘着领导的专车来取书,带着讨好的笑容。
一周后,伽请我去她办公室坐,告诉我,她将我的书放在她的书上面,她跟领导说是我要赠书给他,稍带她将她的书也赠上。她说,这是人间的江湖。我望着眼前的伽,骤起的寒意传遍四肢百骸。我想起了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她命女仆将毒蛇藏在无花果下面,果篮轻巧柔美,伊丽莎白.泰勒蓝灰色的眼睛蛊惑动人。我眼前的伽是小眼睛,耳垂很大,有连接到嘴角的架势。看相的人说她会官运亨通,我信。
此时的我已不带眼镜,留着瀑布一样的长发。我站在父亲的遗像前,看着跳动的火焰明灭着新书的书页,写作是我纪念他的方式。我开始煮汤,鲜排骨、白莲藕、红枸杞,加大锅的水。黄昏时分,我来到阳台,在窗外连绵的晚霞中寻找若隐若现的夕阳,想念着玉琴,深深。
【作者简介】
紫薰,真实姓名:陈丹洁。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上海奉贤作家协会理事、副秘书长。出版散文集《斜倚轩窗》、《四时常相见》,散文集《斜倚轩窗》载入当年《上海文化年鉴》。
[责任编辑 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