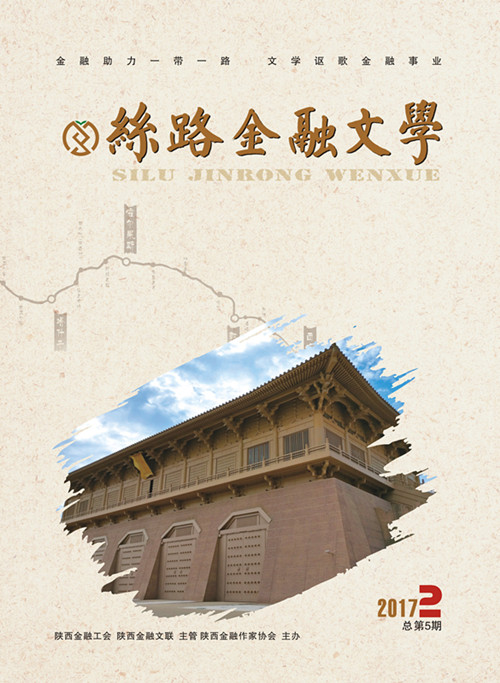嗷--嗷—
娃娃睡觉觉,
山上下来个老道道,
头上戴个草帽帽,
腰里系个草葽葽(用草编的绳子)。
这是一首摇篮曲,是母亲给我灌入的最早最美妙的耳音。
母亲没有文化,也没有编曲的本领,这首摇篮曲一定有它的出处,传到母亲这里或许已流唱了几百年,是否有别的版本?因为从没听别人唱过,权当孤本,我便认作是母亲的摇篮曲了。
音色清丽的母亲一辈子羞于歌唱,她一生辛苦劳作,用这首简单的摇篮曲哄大了十几个子孙。母亲去世十年了,想起母亲时那定格的音容便在眼前浮现。飞针引线的粗糙大手,停泊睡眼迷离孩子的双盘腿小船,浓浓的陕北鼻音,蒙古长调似的低沉婉转摇篮曲。。。。。。想起母亲,冥冥中那天籁之音便划过天际回响在耳畔,仿佛夜朦胧,月朦胧,人也痴呆醉意朦胧了。
幼时,白天常爬上大院一颗歪脖树杈呆坐看天,风在林梢,鸟在叫,云儿在变换飘动,看累了,便像掏空了心一样恍恍惚惚回家。躺在炕上,枕着母亲的腿弯睡觉,母亲手里纳着鞋底,翘起翘落的腿如船桨有节奏地在划动,她哼唱起摇篮曲,带我到流淌的小河里去梦游。
闲暇时,母亲的摇篮曲哼唱的出神入化,不同的心境,她用不同的方式演绎。她随意把某个字吐出长长的拖音,余音淼淼间让人思绪飞扬。幼时,窑洞炕头窗外是南山,南山树木葱茏,在母亲安详的摇篮曲中我经常迷迷糊糊中总是看到南山里的神仙,他们长袍大褂,带着奇形怪状的帽子,时隐时现地在山上小路间穿梭飞行。
WG动乱,人心慌乱,父亲被打倒。有一年冬天,一个县医院人跑的只剩下远离家乡无处可躲的我们一家。记得在一个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晚上。造反派敲打着家门,推搡着父亲去给武斗中炸伤的人去动手术,窗外枪声零乱,伤员哭爹喊娘,母亲熄了灯,黑夜里我们姊妹们浑身颤抖,相互紧挨着和衣躺在炕上,惊恐万状的我们紧紧抱着母亲,为了安抚受到惊吓的孩子,担心父亲安危的母亲拍着我们一个个的肩头低声哼唱起摇篮曲。那悲哀无奈的长调,让风雨飘摇旋转中的小船靠岸,那一夜是那么漫长,母亲反复哼唱的摇篮曲如一首安魂曲让我们度过难忘的一夜。
WG后大哥英年早逝,大嫂改嫁。母亲又一手带大大哥留下的两个孩子。白发苍苍的母亲弯腰驼背,背着侄子,哼唱着她那首摇篮曲在锅台上,庭院里操劳。摇篮曲常常如同陕北说书道情变得急促,戛然而断的字曲中透出迎接苦难的刚毅。
母亲老了,四世同堂,慈善的心依旧要在孩子身上寻找慰藉快乐。抱着重孙子她一脸灿烂,虽然枯瘦如柴的手颤抖的捉不住奶瓶,但依旧会高八度低八度变换声调,哼唱她那永远唱不完的摇篮曲。母亲说社会真好,国泰民安真好,她的摇篮曲不再悲苦,没牙的嘴漏着气,吐出的字模糊不清,而那长调依旧婉转,像孩子一样唱出她的欢心喜悦。
母亲活了八十九岁,老年得了心脏病,年年秋天犯病卧床不起,那年国庆假期赶回伺候她,人因日夜不眠精神错乱,胡言乱语无法入睡。夜里,我抱起轻飘飘憔悴的母亲,让她的头枕在我的臂弯,像她搂着小时的我一样唱起那首熟悉的摇篮曲,可怜的母亲像孩子一样蜷曲在我的怀里不再说话,慢慢合上了浑浊的双眼,两颗豆大的泪滴滑落在苍白的面颊,一脸满足幸福沉沉地进入到梦乡。一首摇篮曲,把母女角色互换,神奇的爱之力量,让我为乌鸦反哺的孝敬体验感到欣慰释怀。
人到中年万事忙,生活的烦恼有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近几年精神衰弱,常常夜不能寐,当思绪杂乱,长夜难眀时,便努力排除杂念专心地一遍遍在心里哼唱母亲的摇篮曲,往往有出奇的效果,它似一味良药也可以医治我的心神不宁。
人生短暂,岁月如歌。今年我做了奶奶,望着怀里的孙女,我又唱起了母亲的摇篮曲。词依旧,曲相近,我却用温暖的长调把爱意恣意抒发,很奇怪,哭闹不止的孙女听我唱摇篮曲先会撇嘴停止哭泣,慢慢便闭了双眼翘起卷曲的睫毛。儿子听我给孙女唱摇篮曲,笑着说他就是听我唱这首歌长大的。是啊,母亲的这首摇篮曲,是世上最动听谐和的音乐,它是生命之歌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我愿它像一条永不干涸的小河,流淌不止,隽永长新。
[责任编辑 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