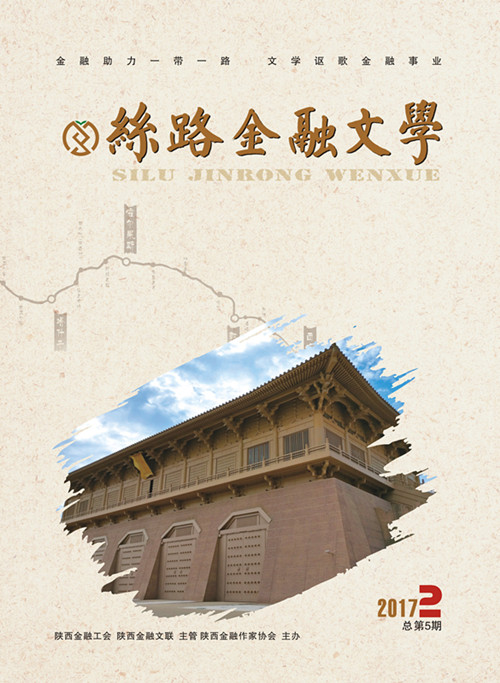烟火中的流年,总有一些故事不曾走远。每每回首起来如散落在天际的星子,在季节轮回的歌声里辗转飞扬。
——题记
我的父亲出生在陕西武功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随后我的奶奶又相继生了三男两女,总共姊妹7个。
我爷爷在48岁时,因病不幸去世,我奶奶一人守寡养活7个子女,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为了5个男孩都能活命,将来也能娶上媳妇,无奈,最终奶奶忍痛将四叔、五叔送了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家不幸被评为地主,父亲也被迫辍学在家,从此,成分问题像一层厚厚的乌云笼罩在我家头顶,一家人整天担惊受怕。三个男孩眼看着一天天长大,却订不下媳妇,奶奶整天以泪洗面。后经人介绍,我父亲才找了个同样是地主成分,一样有姊妹7个的王姓人家的小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
听母亲讲,他和父亲结婚前就见过一次面,谈了20分钟的话,第二次见面时就由大舅妈领着办理了结婚证。父亲与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于1972年的正月初四正式结了婚。母亲说,那天天气异常寒冷,空中飘着鹅毛大雪。父亲步行10余里一步一滑地将母亲接回了家,空中的雪花是上天为他们绽放的婚礼礼花。父亲家与母亲家走小路也要相隔10里路,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10里路可真不短,外婆真不忍心将母亲远嫁西山(其实并没有山,而是母亲家在东边,地势高一些,人叫东岸子,父亲家在西边,地势相对低一些,又相隔10里远,母亲家那边人把父亲住的村子称“西山”),但也是因为成分问题确实没办法。
就这样,母亲背着一床棉被及简单的陪嫁品进了父亲家门,也就是这一床棉被承载了父母一生的幸福和温暖。
这条棉被是由一条大红色的织锦缎面和纯白色手织粗布里子,中间填充着自己家攒了几年的棉花手工缝制而成的,被面上的图案是一条中国人喜欢的神物“龙和凤”,寓意着龙凤呈祥。被面规格要比现在的1.5米床铺盖的尺寸稍小一些,原因是那时候在我们关中老家,家家户户睡得都是土炕,土炕一般窄而长。这床窄而长的结婚嫁妆虽没有现在的棉被松软、轻巧,但特别厚实、缓和、喜庆。听母亲讲,那时为买这条织锦缎被面可费了不少神,还是当时在西安工作的大舅托人从外地捎回来的。母亲的另一件陪嫁品是一条褥子,褥面是天蓝色的洋布底子上一条条红色的鲤鱼活灵活现的游来游去,寓意着鲤鱼跳龙门。母亲的这一床仅有的陪嫁品真的最后也如图案上的寓意一样,为我家带来了好运。
奶奶看着母亲陪嫁的棉被比自己为父亲结婚缝制被面好,让母亲将嫁妆收起来,先不要盖,等逢年过节或重大节日再拿出来盖。后来,不管是父亲去修宝鸡峡水库,还是当民办教师,以至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第二年考上西安财经学院(现在的交通大学),每走一处,背的行李中,都少不了母亲陪嫁的这床仅有的棉被,它凝聚着全家人的期盼与幸福,更凝结着母亲一份沉甸甸的爱。
父亲与母亲的结合看似门当户对,其实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纯属媒妁之言,父母意愿。而且母亲当时没有上过几天学,而后来父亲却幸运的上了大学,再后来进了银行,凭着自身实力一路打拼,走上了领导岗位,而母亲却大字不识几个,但母亲为人善良、勤劳、朴实,一直在家照顾老人、小孩,还要去生产队挣工分,供养父亲上大学,几乎所有的家务活全靠母亲一个人干,瘦高的个子也让扁担压得有些驼背。所以,这也许就是父亲后来无论官做多大,始终没有嫌弃我的母亲,反而不离不弃,让亲朋好友羡慕不已。
1995年,我也有幸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临走前,母亲还是将她那条唯一的,也是盖了几十年的陪嫁品拆洗了一番,又让我拿上,因为时间太长,缎面已严重褪色,失去了往日的光鲜和艳丽,里面的棉花也成了绦子,没有了当初的松软,所以母亲专门买了一条粉色的被套套在上面。我对母亲说,现在都啥年代了,还让我拿这旧被子,咱好歹也是一堂堂大行行长的千金,盖这岂不让同学笑掉大牙了,话音刚落,我看到不善言谈的母亲顿时脸色变了,赶忙说:“好、好、好,您别生气了,我拿上就是了嘛。”其实,我心里明白,这床被子不管再旧,在母亲眼里都是最漂亮的,是她心中最美的“嫁妆”,也可谓我家的“传家宝”,比什么都珍贵!
就这样,这床旧棉被直到我参加工作一直都伴随着我,它已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棉被,而成了我家世代相传的“老古董”了,它既承载着父母的爱情以及我们家族的历史变迁,更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美好而珍贵的回忆。
现在每每家人团聚,父亲总是调侃的说一句:“你妈当年是背着一床铺盖入社来的”,而母亲总是默不作声,但一脸的幸福。这时,我总会在一旁迫不及待的插一句:“正是由于我妈的这一床被子为你遮风挡雨、御寒取暖,才带来了一生的好运和幸福,我妈才是咱家的大福星呢”,全家人顿时哈哈大笑,其乐融融。
细数那条旧棉被陪伴我们的过往,那些平淡的岁月,才是我记忆中最美的时光。
[责任编辑 鲁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