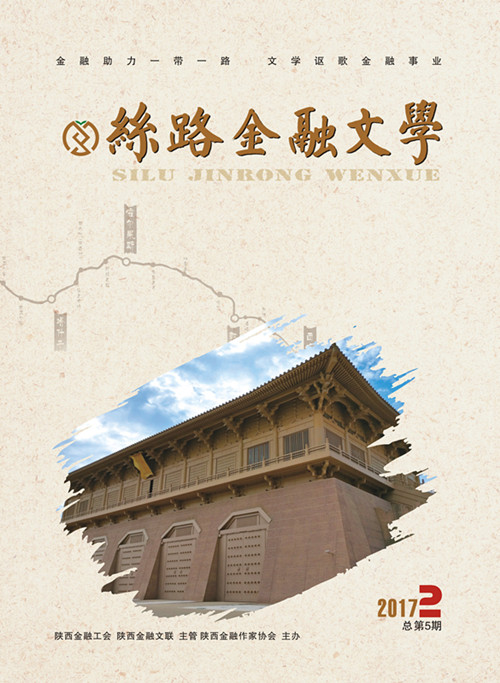王:和谷老师,您在报告文学和散文创作两个领域都有不菲的成就,您更喜欢哪一个文体?这两个体裁您个人对哪一个更投入一点,或者说给您带来怎样不同的感觉?
和:更喜欢写散文。更投入一点的是报告文字,或称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散文往往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理,信马由缰,精神上是自由的、愉悦的,是心灵的释放与挥洒,完全非功利的,是对生活艺术的审美享受。报告文学则需要有意义的选题,现场踏勘采访,搜寻梳理素材资料,原则上做到无一字无出处,也就是真实性吧。尽可能做到用简约的文字,把事情叙写清楚,融思想于其间,语言艺术上考究在次。其社会现实功用与价值,较散文属于另一路笔法,相对费力,尤其是长篇纪实文学。
王:从当年久负盛名的《市长张铁民》到《音乐家赵季平》等,这么多报告文学在采访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写作别人的真实故事对于您个人的意义?
和:写市长张铁民时,三十郎当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尽管主人公有口碑却也是个颇受非议的人物,出自担当敢为便写了。赞誉背后,无形的政坛诟病却让作者走南闯北,困惑多年而不解,然而便也无悔。赵季平是我供职单位的文艺官员,是大艺术家,同事数年,耳濡目染,对其知之甚多也甚细密,有兴趣写他,写起来得心应手。他是明白人,只是对书稿中的人名、时间、地点、音乐术语和理论性阐述作个别校正,写什么怎么写则尊重作者笔墨,这也就顺当并省事多了。写别人的故事,让我增加见识,钦佩主人公的人格力量,自己也被感化,写别人亦是写自己。
王:您的散文集《还乡札记》获柳青文学奖,长篇散文《归园》在2013年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近些年,“还乡”这个词可能更多的出现在您的情怀当中,您在铜川老家南凹也修葺了一处院落,时不时回去小住。您觉得这是人精神的必然吗?写作更主要是对家乡的致意还是对自己的安慰?
和:具象与抽象的还乡,的确是人精神的必然归宿。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如陈忠实所慨叹的“老友相继凋零,倍感人生匆促”,还乡则是缓解这种生命痛楚的中草药。向家乡致意,与自我抚慰是一致的,回归故园,赤子的脚板与清新的泥土是彼此重吻的。
王:散文集《秦岭论语》获冰心散文奖,秦岭是每一个生活在秦地的人不可或缺的地理象征,您是在通过这本书梳理自己的地理情感和由此带来的种种心理的微妙吗?
和:梳理人文地理及地域概念的秦岭,观照的是自然和历史文明进程中的意味,亦是对人在生存环境中的惊喜与迷惑的探寻。包括现代人在这一话题中的微妙的心理处境。书名只是其中一篇作品的篇名,不是系统论述,包括了多篇如《司马祠》、《唐长安》、《汉江源记》、《云南十日》、《西藏散记》等散文作品。但力诫不要写成走马观花、浮皮潦草的游记文字。
王:您是舞剧《白鹿原》的编剧,曾经有林兆华导演的话剧,还有去年上映的电影,观众褒贬不一。您是怎样在线索众多的剧情中把握表现呢?
和:话剧版注重众多人物在场景中的呈现和渲染,舞剧《白鹿原》则用优雅的肢体艺术语言来表现原著精神品质,大胆且简洁地从厚重繁复的小说文本中,抽出一条纠结全书的人物小娥作为剧情的主角,演绎她与几个男人的情感纠葛和命运,更贴近舞剧的舞台空间形式。稍后的电影版,镜头也是偏重于小娥的剧情,就显得不尽人意了。
王:您写《渭河,你好吗》,近些年“自然”也是您关注的重点吗?
和:我在获自然写作奖感言说过,我的写作或远或近一直未离开过与自然的关系。着重写自然生态的报告文学,是整版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库布其,绿色琴弦》,是写黄河河套治沙景观的。多是在乡间僻野溜达,关切农时节气,与庄稼果树杂草一类植物交谈,写点原上花花草草的博文而已。
王:写作《市长张铁民》应该是您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尤其是在现在的环境中,您留下了一个好市长的宝贵故事,如今想起来,有什么感触?
和:前多年,有人说《市长张铁民》是我的代表作,我还不以为然,自己更偏爱于《游子吟》、《黄河古渡》、《长安梦寻》、《王维的辋川》等散文。报告文学注重思想性,文学价值相对弱一些,不被我看重,但通过改编电视剧在央视呈现,知者甚众且流传久远,美文反而小众,我似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张铁民是一个好市长,一个真正为民执政的共产党官员,他的故事是一面镜子,是眼下廉政者的写照,也反衬出腐败者丑陋无耻的面孔。
王:每一部报告文学都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写作关中民俗博物院创立者王勇超的报告文学《国风》,应该也是非常有故事的过程,能给大家讲讲吗?
和:《国风》的主人公王勇超是柳青笔下梁生宝的后一代农民乡党,揣着十块钱进城打工,近三十年后拥有了一座估值十个亿的关中民俗博物院,显示出民间文化的自觉自信,其奇值得一书。采访写作历时四载,数易其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有评论家给予中肯的评价,深解个中三昧,也有读者被豪华版本的图像遮蔽,未细读文字,误为是给私企做广告宣传,忽略了民风即国风,如苏轼所言“国之长短在风俗”的蕴意。
王:您写过《巴黎望乡》,为什么沉浸在国外的文化当中,要“望乡”呢?拉开距离以后,故乡在心中的位置和感觉是怎样的?
和:《巴黎望乡》是客居海南岛时游历西欧的随笔集,身居异乡方可回望故乡,不然则井底之蛙,不识庐山真面目。望乡,似乎是今生今世的一个精神的死结,扯不断理还乱。年少时离开故土,生活在别处,愈行愈远,漂泊得一头白发,满怀疲惫,泪水酸楚,诗意的安居何在?原来,距离产生美,万乐与本源为邻,故乡奥妙而美丽。你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却也回归最早出发的地方,而当初的离乡并非错误。如圣经所说,你本来就是在世上客旅客居的,若想念永恒的家乡,回去便是了。
王:书法绘画也一直是您喜爱的,我看过一幅《故园》,温情,松弛,但很笃定。书法和绘画在您的创作生活当中是什么角色呢?
和:我一直喜好书法绘画,只是喜好,从未想去跨界抢坐书法家画家的板凳。我的书画也有传播,皆属习作,处于摹写或调试水墨关系阶段。博彩众长,偏好苛刻,也只是在作文的闲暇之余自我休憩的一种转换方式。书画与诗文相通,技术性重要,但贵在意味与情调。更多的是孤芳自赏,与书坛画派没大的干系,也与纯商品性无涉。
王:您有没有什么写作习惯?现在是每天都写吗?
和:十多年来习惯了电脑写作,操作简便,如果仍用笔纸写,尤其是长篇纪
实作品,简直匪夷所思。我同时有几部长篇纪实参差推进,思维变调不受影响,短篇插空即成。除公务审看影视或不多的应酬和还乡赋闲时间外,均稳坐窗下梳理素材,开写修改阶段每天约三千字进度。年过花甲,写作成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瘾似的,说是罢笔,却不能自拔。
王:目前正在创作什么?《柳公权》吗?
和:有《归园》、《丝绸路上》、《习仲勋人生纪实》、《照金往事》、《汉江之子》五部长篇散文或纪实书稿,已交稿待出版或在修订中,约一百二十多万字。长篇传记《柳公权》,已进入完善史料及调整提纲阶段,春暖花开时动笔,力争按与中国作协合同期限,年底交稿。《柳公权》是块硬骨头,亦是深水区,颇有压力,却富于诱惑。
王:您在《从心集》序言中写:耳顺挺好,从心所欲不越法度也好,粗茶淡饭,一杯茶,一本书,如此晚年该知足了。其实人都是从繁华归于简单的,值得在意的就是身边的事和人,可能这时候才获得真正的开阔。您现在的心境能描述一下吗?
和:还是那句从心所欲不越法度的话,缩小人际圈子,少于应酬,如鲁迅所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在静静的小角落里,做一点自己愿意做而且做起来愉悦的事,渐渐老去。
王:您这样在《音乐家赵季平》后记中写道:写官员与艺术家,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又说:能写出一个在尘世上的人,其心灵的挣扎与快慰,同时感染了周围更多的人,好好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便是文学写作的意义,也是人们与读物之间的意味所在。我觉得说得太好了。您觉得写作还有什么您割舍不下的意义所在呢?
和:文学写作关注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进程,人的情感处境,无论哪种表现形式,其文化立场和学养品行,决定写作的意义与价值。割舍不下的是,一息尚存,仍然求索写作和人生的真正意义,而已。